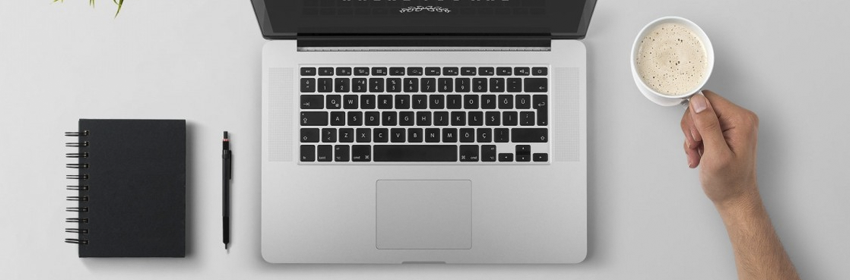電視機裡的雪花是宇宙誕生時的餘暉、頭部按摩器是宇宙信號接收器、主人公會往宇宙功德箱裡投520塊錢來買看硅膠外星人的機會、頭頂鋁鍋的少年會乘著烏鴉遠走消失……
4月1日,高分口碑之作《宇宙探索編輯部》上映,片中天馬行空的想象力、奇奇怪怪的腦洞不僅好笑,也很浪漫。
這部郭帆導演監製的作品,雖然自嘲為“科幻電影地板磚”,實則在與《流浪地球》系列完全不同的維度上,探索了科幻電影更多的可能性,也觸碰到科幻最本質的內核:宇宙和人類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甚至不應該將其囿於科幻片的範疇裡進行討論,這本身就是一種很新的電影,導演孔大山的長片處女作,讓觀眾看到了90後的新一代導演們突破傳統的能力。

究竟是怎樣的導演能拍出如此“神經病”的電影?那些可可愛愛的腦洞是如何誕生的?這部電影討論的本質又是什麼?
娛理工作室與導演孔大山、監製王紅衛交流後,用20個小故事告訴你答案。
第一章 貼地飛行的人

在《宇宙探索編輯部》的首映禮上,李雪琴透露了他第一次和孔大山見面的經歷。當時孔大山問她,“你有病嗎?”李雪琴以為藝術家都是這麼打招呼的,於是回答,“我有病。”孔大山說,“太好了,我也有病,我一看你就有病。”
拍出這樣一部腦洞大開的電影,孔大山給外界的印象可能就是這樣一個“有病”、有點神經質的人。
但本片監製,也是孔大山的研究生導師王紅衛則表示,其實日常生活中的孔大山更明顯的特徵是社恐,“跟他路演的時候類似,就是一個話不多、不善於聊天的一個小孩”。


生活中不善言辭的孔大山,在拍電影這件事上卻展現出很高的化緣能力。
他在平遙影展上看過王一通的片子,於是把他拉過來做了編劇和主演,攝影師也是在平遙影展上聊天時偶遇的。
從社恐變社牛,孔大山表示:“我只是不太善於面對公眾或者是人多的場面,特別是工作性質的交流我就不自覺地會謹言慎行,在私下裡如果我發現我們有共同話題,其實幾句話就能建立連接。所以跟王一通是連面都沒見,我光看片子就知道他一定是我的好朋友。攝影師老馬當時我雖然沒看到片子,但是聊天的時候他開的玩笑我覺得很同頻,我倆喜歡的導演也很接近,比如考里斯馬基。”


郭帆導演在聊起《流浪地球》的成功經驗時,多次提起文化語境和共情的問題,孔大山則表示沒有特別考慮這一點,因為自己本身就很接地氣。
“我也不是仙風道骨的藝術家,我需要來接地氣,我本來就趴在地上的,我是貼地飛行的民間導演,完全就是出於我跟王一通本能的惡趣味就寫了這個故事。”
對於自己的風格,孔大山的形容是“一本正經地胡說八道”。
這種審美上的“惡趣味”是如何形成的?孔大山用天生的幽默感回應這個問題,“我之前報了個班,幽默感培訓班。”


《宇宙探索編輯部》被孔大山定義為“民間科幻片”,長片處女作選擇了科幻題材,但孔大山的電影啟蒙並不是科幻片。
“我不像郭帆導演他的電影啟蒙就是科幻片,他是看了《終結者2》想要當一個導演,我小時候也看這部電影也很喜歡,但是我不會覺得這個電影跟我有什麼關係,也不會萌生出我也想要拍這樣的電影的想法,我覺得太遙遠了。
我真正萌生當導演的念頭是看賈樟柯導演的《小武》,我看到那樣一個呈現的世界,才覺得這個是跟我有關係的。”


孔大山和監製郭帆的緣分開始於《李獻計歷險記》。孔大山大學畢業後拍了部短片《少年馬力傲的煩惱》,改編的就是郭帆導演的這部電影。後來郭帆在網上看到了,兩人就網友面基。
用孔大山的話來說,“我是屬於民科,郭帆導演是科學家,他可能需要一個民科來調劑一下。”

第二章 拍片難

《宇宙探索編輯部》選用了偽紀錄片式的拍攝方法,孔大山表示,這來源於他在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第一課,王紅衛老師訓練他們拍攝偽紀錄片。
王紅衛說,這個教學的目的是訓練新導演的電影感,“對於一個做電影的人,電影感是根本性的事兒,否則最終他走不遠的,他只能拍一個商品供當下去消費,從文牧野他們班也就是2010年的時候,我第一次試著用這種方法,因為偽紀錄有一個特點,就是這個事兒它是虛構的,但是你拍出來讓人感覺是真的,所有電影從底層邏輯都是這個要求。”
偽紀錄的形態是一開始就確定的,但當時王紅衛和孔大山都心裡沒底,不知道這個文本層面成立的想法,拍出來能不能成立。
王紅衛說,“我看完劇本和聽完他的整個計劃後,我會擔心他做不成這個樣子,我們會擔心他做的更像傳統的虛構的劇情片,但是他覺得他有信心,看完他第一遍的粗剪我已經覺得這是電影應該有的樣子、是他想象中的樣子、也是我很滿意的一個樣子,他把一個非常有挑戰性有難度的東西完成了。”


《宇宙探索編輯部》的故事緣起於一條新聞,講的是一個村民說他藏了外星人,結果打開冰櫃,裡面是一個硅膠做得特別劣質的“外星人”。郭帆就和孔大山聊,說為什麼這個看起來假假的外星人不能是真的外星人,電影就是從這個基礎上延展的。
劇本從這條新聞延展成約5000字的劇本大綱,孔大山用了差不多10個月的時間。
孔大山表示,之所以需要這麼多時間,是因為越寫就越意識到這個故事細節量的龐大,“因為你不能像寫一個特別風格化的電影,用那種極簡主義的感覺去寫一場戲,這場戲所有演員就是沒有表情,沒有動作或者沒有臺詞,只要有一些狀態就行了,我這個電影是偽紀錄片,意味著你要呈現一種生活的質感,生活的質感就意味著無數的細節要去堆積,才能出現這種感覺,所以這其實挺耗費精力的。”


電影裡艾麗婭飾演的秦彩蓉被狗咬之後,眾人垂頭喪氣地坐在一個倉庫裡,最後成片中剪到只剩一個鏡頭,實際上拍攝時這裡有一場長達8分鐘的對話戲,也是片中唯一一場用了飛頁的戲。
“對話戲主要聚焦的是主人公唐志軍跟那個女孩曉曉的衝突矛盾,其實曉曉這個角色是投射成唐志軍女兒的性質,就是想完成一個唐志軍和女兒在現實中的一種對話,去加重他們之間的衝突,去表達他們之間的這種矛盾、不理解。
但是那場戲寫的時候就沒寫好,拍的時候很費勁,拍了第一天就覺得不對,當天晚上就改,改完之後第二天晚上又接著拍,拍完我覺得還是不對,只能寄希望於靠剪輯能剪出來,後來發現也剪不出來,最後發現是劇本層面存在的問題,劇本就不該那麼寫,那麼寫的話就很尷尬,就很刻意。”


孔大山曾經說過,“拍電影很難,就像在地球上尋找外星人”,但如今他表示,特別想賽博消除這句話,因為現在想想,幹啥都不容易,拍電影沒啥好抱怨的。
拍戲的難不應該去訴苦,但是可以分享一些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孔大山表示,因為電影的類型是公路片,所以最大的困難就是轉場和一路的顛沛流離。
“你要在各種路途坎坷的過程中去完成創作,比如我們有大的轉場是從北京到成都,火車上的戲份就是劇組真的在轉場的火車上拍的,包括你看到所有的交通工具的戲份,都是我們真的在轉場的過程中去拍。所以就特別慌亂了,下車還拎著行李,然後趕緊行李扔一邊去拍戲,拍完之後再上車去趕路。成都到宜賓到大涼山到雅安就是大的轉場,然後每個地方還有無數小的轉場,從一個城市這個村到另外一個村,或者從這個村到另外一個山林,還要克服各種當地的自然條件和惡劣的天氣,這些是特別困擾的。”

王紅衛透露,這部戲錢不多,又涉及到大量的轉場拍攝,且拍攝的條件非常艱苦,所以這個過程其實是“一天天一邊熬著,一邊跟自己的意志力做鬥爭,跟全組可能出現的各種意外情況做鬥爭,一邊還要去保證你的藝術的想法儘可能地實現。”
在王紅衛看來,孔大山拍《宇宙探索編輯部》的過程很像當年甯浩拍《綠草地》,都是錢不多,且拍攝環境艱苦複雜,“很多青年導演都經歷過這個過程,這不僅僅是對你專業水平的一個考驗,更多是對你的意志力、你對這個片子的希望和信心的一個考驗。”

電影殺青的那天晚上,孔大山第一反應是想跑路:“我覺得拍了一堆莫名其妙的玩意兒,花了那麼多錢浪費了那麼多時間,耗費了這麼多人的心血,我覺得辜負了郭帆導演和王紅衛老師對我的期盼和信任,又騙了他們,我拍這些東西根本就一堆垃圾,當時真的這種感受,以至於在殺青之後的一個月裡,我都不敢去機房,我不想面對這些素材。
所以我跟剪輯師說你先剪,我去郭導那兒開會,我跟郭導說我在機房在剪片子,其實我在家裡自己打遊戲,那時候就兩頭騙哈哈,就一直不敢面對這個事。”
後來剪輯師花了一個多月剪出來一個粗剪版本,孔大山看到了某些段落覺得好像有戲、沒有想象中那麼糟糕,然後就開始自己參與剪輯,在那個過程中也慢慢找回了信心。
創作劇本時,孔大山加了很多UFO愛好者的群,有一天看到了一個首屆星際文明探索論壇的廣告,於是斥700塊錢巨資購入門票。
在大會上孔大山發現,這裡聚集的是全中國最頂尖的UFO專家以及愛好者們,這群人對世界和宇宙有不一樣的理解,比如會覺得自己的老家在一顆遙遠的星球,在等著老家來人把他們接回去。
孔大山說,自己在這群人面前其實很忐忑,“因為我就像一個臥底潛伏,生怕被他們用腦電波識別出來這有一個臥底。“
為了給劇本取材,孔大山又需要跟一個實實在在的人進行一對一的真實交流,最終他找到了崔大姐,告訴她自己在拍電影的事,最後還邀請她加入編輯部出演了一個角色。
“當時是大會上有問答環節,我和王一通聽到崔大姐的提問,覺得她有點東西,散會就去找她聊天,跟她說我做導演拍電影,她就問這個電影是電的影子,那麼它的本體是什麼?我就一時語塞,然後崔大姐就開始長達半小時的freestyle,瘋狂給我輸出,從宇宙到量子力學到區塊鏈到陰陽五行,知識結構完全突破了我的所有讀物對科學物理學對世界的認知,我當時還拍了原始素材,我就覺得一定要讓她當演員。
所以我就把她寫在了電影裡頭,她在編輯部自言自語的所有的內容都是她自己的即興,我沒有給她寫任何詞,我在現場就跟她說,崔阿姨你可以開始說話了。”
另一個沒有臺詞的演員是郭帆導演,在《宇宙探索編輯部》中作為《流浪的球》的導演友情客串。
導演郭帆的演技如何?孔大山表示:“他一進入狀態就挺對的,因為他太知道我這個片子的風格,他不需要去很戲劇性地起範兒,他就演一個疲憊的導演、不情願的導演。唯一費勁的是他在擺弄宇航服的時候有個東西突然掉下來,看起來是不經意的事,其實是個難點。你要拍出這種不經意掉落的一瞬間,捕捉到當時的那種尷尬感,所以那條拍了得十五六條。”
孔大山表示,宇宙功德箱靈感來源於小時候看周星馳電影《破壞之王》中的“人人有功練功德箱”、孫一通頭頂的鋁鍋來源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氣功熱時的現象,“那是一個既有印象,我最早就一直想說我以後拍電影一定要把這個鍋的造型拍到電影裡去,只不過這次電影剛好就很契合。”
其他的諸如唐志軍的宇宙信號接收器、代表著宇宙誕生時餘暉的雪花電視機等等,則是孔大山和王一通頭腦風暴想出來的。
《宇宙探索編輯部》中不乏奇思妙想,但有一句臺詞是孔大山至今回想都覺得是靈光乍現的神來之筆——
「猴子把外星人的腿骨遞給我,問我有桃嗎?我說沒有,猴子說麻嘞批。」
孔大山說:“疫情之後,我們停機的那段時間,我又改了一輪劇本,猴子這場戲其實是我唯一寫劇本的時候,自己把自己寫笑了的一場戲,因為我覺得太嗨了,我太喜歡猴子了。我記得當時寫完我還發到了三個人的策劃群裡,我說快看,太好笑了!”
電影中的詩都是編劇兼主演王一通的原創。孔大山表示,自由創作的前提是要以孫一通這個角色的身份去創作,而不是以王一通的身份去寫詩。
“前期的那些詩歌我沒有什麼要求,就他自己發揮,我會把他寫的詩裡我喜歡的段落直接拼貼進片子,比如這首詩的這幾句我喜歡,我就把這幾句單獨摘出來,跟另外一首詩的另外幾句拼接在一起。
最後山洞裡那首詩我參與了一部分,因為我覺得最後那個詩不能只是詩歌本身了,它必須要承載一些劇作的意義,第一要跟劇情和主題勾連,第二就是還要形成韻律感、節奏感、成為音樂的一部分。”
塑造唐志軍這個主人公前,孔大山和演員楊皓宇詳細討論了這個人物的世界觀、價值觀,詳細到他什麼事能做、什麼事肯定不會做。
舉個例子,唐志軍不能太隨意,不能有生活化的一些流露,在吃麵條那種戲裡,唐志軍不會注意這碗麵條怎麼樣,在他的認知系統裡,這不是麵條,就是碳水化合物,是維持生命運轉的一種營養物質,類似於這樣的一種認知上的細節,孔大山會跟楊皓宇去傳達和探討。
在表演的細節上,需要他在舉手投足中把握住特別微妙的一些分寸感,比如說話時的緊張感、頓挫感、渾身肌肉都是緊繃的狀態,手很僵硬地懸浮在身體兩邊的肢體狀態,都是塑造這個人物很重要的元素。
在世俗的眼光裡,唐志軍可能不是一個正常人,但誰又有資格定義正常和不正常呢?孔大山說,“是不是正常也是多數人的暴政?所以我們是想去呈現另一種可能性。”
孔大山的生活裡沒有唐志軍這樣的人物,他說,“就算有這樣的人,可能我也沒有資格認識他。”
片中秦彩蓉對唐志軍的定義是“民科”。在孔大山看來,民科其實是“一群內心有自我特別篤定的信念的人,他們在精神世界裡是自洽的,但是跟現實世界又是脫軌的。”
《宇宙探索編輯部》深受一部叫《自行車與舊電鋼》的紀錄電影的影響,裡面的主人公就是跟這個世界格格不入,在外人眼中他是失敗者甚至神經病,但在他的精神世界裡,他會覺得自己是巴赫是上帝,自得其樂,孔大山認為這種狀態特別讓人羨慕。
唐志軍這個人物被很多觀眾解讀為仰望星空的理想主義者,但孔大山表示,這其實有些美化他了。
“平遙的時候有媒體採訪我,採訪之前我看了電影在網上的評論,網友就說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輓歌,然後我就被洗腦了。媒體問我唐志軍是個怎樣的人,我就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後來我想根本就不是,我在寫的時候根本沒想到他是一個所謂的理想主義者,或者想拍關於理想主義者去實現理想的故事,我覺得我真正想拍的就是一個偏執狂,如何自我和解的故事。”
孔大山認為,這種偏執狂天然有美學性,自帶戲劇張力,他的執念和現實是錯位的,他如何去縫合現實之間的錯位,就是故事的戲劇性所在。
在路演中,孔大山被問的最多的問題是故事的緣起是什麼、為什麼用偽紀錄片的拍攝手法,他說這些只是重複的問題,他更怕的是問他宇宙的意義是什麼、人類存在的意義是什麼,“我覺得我已經用一個118分的電影告訴你大家了,就何必再問我。”
至於宇宙的盡頭是什麼,孔大山的答案就是DNA,觀眾怎麼去理解DNA、怎麼理解生命和宇宙,就交給觀眾了,每一個觀眾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解讀。
《宇宙探索編輯部》的首映禮上,王紅衛表示,從市場角度來看,一些觀眾對於影片的觀影反饋可能是覺得“很怪”,但作為一個看了很多學生作品的老師,同時,也作為一個一直希望有更新東西出現的電影人,他覺得這部電影還是挺正常的。
著名編劇張冀說,從這句話中能確定電影學院是出了一批人才,人才一定是一批批的,不是一個個的。“中國電影現在非常保守,應該看到更多這樣的片子。在紅衛老師和郭帆老師的體系裡,他們在突破現在已經陳舊的電影語法和創作。你們告訴所有的人,電影必須創新,必須講我們想講的。”
王紅衛說,孔大山其實是他帶的第一屆90後的研究生,他很希望《宇宙探索編輯部》的出發意味著90後有一代新人成長起來了。
“他們的一些想法能夠更進一步脫離比較傳統的思維審美,去做比較新的電影,這個很難,但是他總得做,總不能我們永遠在拍老電影。
我覺得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還是得從電影的發端,從作者開始,不是我們整天去說環境怎麼樣、審查怎麼樣、觀眾怎麼樣,所有的創意產業從來是靠作者驅動的,必須是這些學導演的學電影的孩子,自己有很強烈的慾望去做,而且他敢做、他能做、你也支持他做,從這些源頭上游才可能去促成一些更新換代,才可能促成一些新的電影,甚至於新的美學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