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公眾號點擊右上角“…”設置星標 ↓
防止內容走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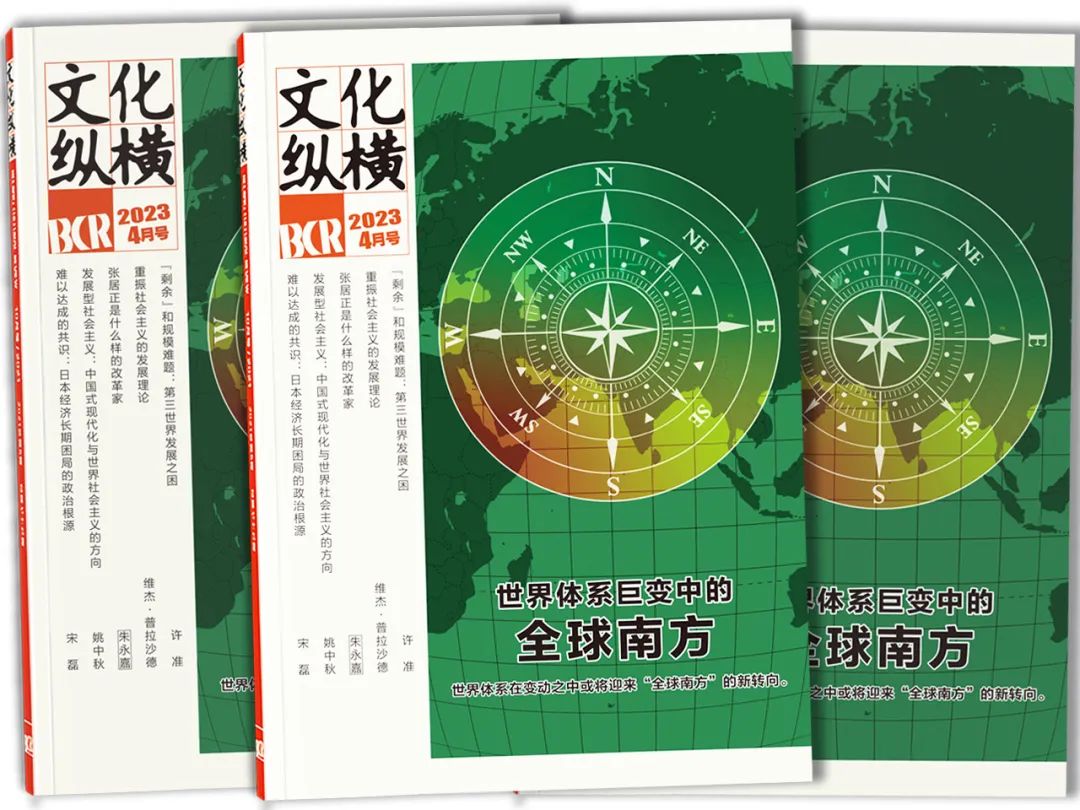
貧困人群無法成為開發扶貧過程中的發展主體,主要是因為貧困人群存在所謂的能力問題而受到排斥。貧困人群所欠缺的能力又主要是指發展生產以及市場銷售的能力。貧困人群本來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在地者,除了智障體殘人士,他們作為長期與土地打交道的直接生產者,應該最為稔熟在地農產品的生產經驗以及家庭日常消費之餘的農產品的自主銷售渠道。在此,我們應該思考的並非如何提高貧困人群發展生產以及市場銷售的能力,而是貧困人群為什麼喪失了這一能力。
在開發扶貧的過程中,規模化的市場經濟的合理性被無可置疑地加以預設,農民在地的傳統生產方式也相應地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障礙。本來各地農民都會根據日常生活需要、傳統習慣、氣候條件,在有限的耕地上輪作、套種多品種、小規模的農產品,但這在開發扶貧的思路里屬於沒有效率的、無法給貧困人群增加收入的保守農業。經歷過早年有些地方政府“逼民致富”大規模種植經濟作物而最終因銷售渠道不暢導致農民虧本的慘痛教訓之後,今天地方政府則大力推行“公司+農戶”的開發扶貧模式。“公司+農戶”的實質是公司將農業生產的風險轉嫁到農戶頭上,同時控制農業生產的產前、產後環節並獲取利潤。因為公司與農戶之間存在嚴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關係,所以,如果市場的零售價格高於公司的收購價格,農戶也會為自己的利益考慮而將部分農產品直接賣到周邊市場上。
為此,公司往往選擇那些適宜在當地種植但又不為當地市場接受或者不屬於在地人群飲食習慣範圍內的外來農產品或者中草藥,這樣,可以有效防範農戶的自主銷售。這與全球範圍內大型農業企業偏好於拉大產銷地之間距離的做法如出一轍。如武陵山區桑植縣的開發扶貧項目是公司帶動農戶種植高山金錢草,該公司自己加工並設立專賣店銷售;六盤山區西吉縣的開發扶貧項目是公司帶動農戶大規模種植西芹,該公司統一收購加工為易拉罐西芹汁飲料。不管是金錢草還是西芹,都是難以進入在地的日常消費的,也是缺乏在地的市場需求的。
在“公司+農戶”的扶貧開發項目中,公司越來越趨向選擇大規模種植與在地市場脫節的農產品,這樣,農戶當然只能越來越依靠公司而毫無自主的市場渠道和銷售能力。可以說,如果公司與農戶之間的生產關係沒有改變,那麼,政府對“公司+農戶”的扶貧開發項目的進一步投入,只能進一步鞏固貧困農戶對公司以及資本的依附關係。
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雲南省臨滄市鳳慶縣是省級貧困縣,也是滇紅茶的核心產地,其種植大葉紅茶的歷史悠久。鳳慶縣為山區,平坦耕地匱乏,農民不得不在高達六七十度的陡坡上開發梯田,並摸索出核桃套種茶葉、核桃套種魔芋的獨特種植方法。鳳慶縣共有200多萬畝茶田,農戶大約10萬戶,可是至今沒有一個農業龍頭企業可以成功進駐。農戶在自家兩畝左右的梯田上套種茶葉、核桃、魔芋,在每五天一市集(逢農曆一、六)上行銷,區域內滇紅茶廠的收購價格也無大的波動,農戶並不需要公司的帶動。也有龍頭企業想在當地發動農戶種植澳大利亞金果、臺灣木瓜,但無人響應加入。
同樣的貧困人群,為什麼鳳慶縣的農民就可以解決市場銷售的問題?關鍵在於種植品種多樣化、傳統化、小規模,農產品為在地人群日常消費所樂見,可以在地長銷。我們在烏蒙山區的涼山彝族地區調查時也發現,儘管苦蕎的產量及利潤低,但是當地貧困人群還是堅持種植。正因為產量及利潤低,又是當地的特產,所以外部的農業資本才沒有興趣前來投資生產,從而排除惡性競爭,使得苦蕎在當地市場上保持相對穩定的價格,也使小農戶獲得相對穩定的低收入。這些都屬於內髮型發展強調的“小地區範圍”以及傳統的重要作用,也屬於施堅雅(G.Willian Skinner)強調的基層市場乃是鄉村社會的真正單位,在那裡,基層群眾可以結成社會網絡,利用各種社會資源於生計。
可見,一旦將農民的農業生產架空於在地的傳統種植及傳統飲食需求,農民就會被“去能”,既無種植經驗,又不知道產品銷向何方,淪為一個更加全面的貧困者。因此,“地產地銷”才可以成為全球範圍內底層貧民反抗農業資本入侵的一個口號。
經歷過人民公社時期大興農田水利建設、綠色革命之後,中國的農業基本上告別了靠天吃飯的時代,農業的生產能力實現了革命性的飛躍。20世紀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體,農業生產又回到了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格局;作為政府向農業領域提供的公共產品,諸如興修水利、品種改良、病蟲害防治、因地制宜的農業機械發明等嚴重缺乏。對偏僻貧困地區來說,農業生產又回到了靠天吃飯的時代。貧困人群的農業生產能力如何,這需要其在與其他農業生產主體的比較中得以表現。
今天的情況是,一方面,市場化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幾乎放棄了對農業生產過程的公共產品供給,原來設立於公社(鄉鎮)服務於農業生產的“七站八所”也已經全部市場化,貧困人群只能通過市場途徑尋求必要的農業生產服務,這無疑大大抬高了農業生產成本。在貧困人群缺乏現金的情況下,市場化的農業服務需求必然壓縮,其農業生產能力也無法提高。
另外,各級政府中的農業部門無不青睞農業龍頭企業,紛紛將本來應該投入農業公共產品供給的有限資金向龍頭企業傾斜,低息、貼息或者無償向龍頭企業提供專項資金,幫助其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加大科技投入,修建滴灌噴灌設施等。這樣,貧困小農戶的農業生產能力便完全無法與農業龍頭企業相提並論。在開發扶貧政策的推動下,為了獲得立竿見影的扶貧效果,專項扶貧資金越來越向允諾帶動貧困戶致富的農業龍頭企業匯聚。
開發扶貧尤其是精準扶貧本來應該立足於提高貧困戶的能力,這樣才能有可持續的發展,減少返貧現象的發生。真正與農民生產息息相關的公共服務項目,特別是農業生產所依賴的農田水利、農業技術指導、農作物病蟲害防治等,雖然對貧困群眾而言更有直接針對性和迫切需求性,卻少有扶貧幹部問津。在絕大多數涉農服務部門都圍著大項目轉的情況下,還在從事家庭農業生產的貧困戶難以享受到由政府提供的農業公共服務。基層農業、水利等涉農部門的市場化,極大地增加了貧困人群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成本,擠壓了直接生產者的利潤空間。
在我們調研的途中,常常可見被統計為水田的耕地由於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已經無法灌溉而成為旱地。為此,開發扶貧應該將更多的資金直接投向面向廣大貧困戶的農業生產過程,普惠式地向他們提供家庭農業生產過程中必需的公共產品。同時,不能將提高貧困戶的農業生產能力視為只是扶貧工作的臨時任務,而應該將其常規化、制度化;即使是扶貧工作,也不能將其視為只是外來幫扶單位的事情而與地方政府農業部門無關。從小農農業生產能力提高的角度著想,地方農業部門應該從機關化、官僚化的辦公室走向農業生產一線的田間地頭,將恢復“七站八所”的公益性納入扶貧工作範圍,貼近小農提供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實現真正的精準扶貧。
可見,貧困人群的能力不足問題的產生,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是制度實踐的產物,是被“去能”的結果。我們在開發扶貧工作中與其強調對貧困人群“賦能”,不如致力於防範對貧困人群“去能”,在扶貧資源的分配上避免“壘大戶”。
(本文選自吳重慶著《超越空心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
近年來,隨著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鄉村空心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轉。本書名為《超越空心化》,既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跡象的揭示,也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未來的期待。本書由三部分內容構成,一是立足於“大國小農”的國情農情,研究小農戶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賦能”,關注內髮型發展及縣域城鄉流動;二是聚焦“同鄉同業”現象,剖析經濟活動與鄉土社會網絡如何互嵌以及鄉村空心化的反向運動;三是闡述鄉村空心化、階層分化背景下鄉村社會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鄉村社會的生機。作者通過對“隙地”“狹地”“邊地”的調查,在具體的區域中尋找中國農村,探尋基於激發鄉村內生力量、與城鎮化並行的鄉村發展之路。
本文為合作推廣,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文化縱橫”觀點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