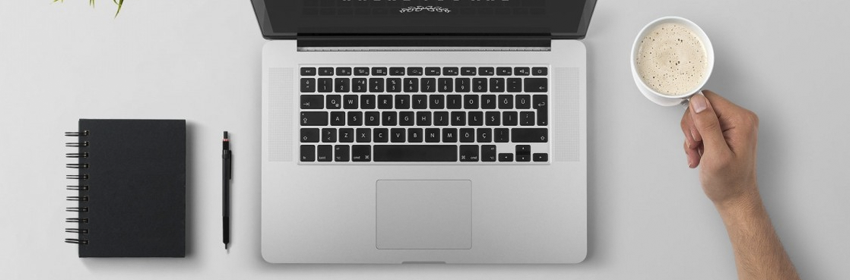人這一輩子長了不過大幾十年,什麼叫活著?
在自己的喜歡裡,那才叫活著。
|作者:高 塬
|排版:徐一冉
一隻狗用十年餘生等待主人——人們對《忠犬八公》的故事太熟悉了,這部“感動全球數億人”的電影,曾先後在日本、美國獲得商業和藝術上的成功,對愛狗人士來說,這是一部核彈級別的催淚瓦斯,哪怕是不養寵物的觀眾看了,也情不自禁潸然淚下。
如今,《忠犬八公》來到中國,擺在導演徐昂眼前的,卻不是一部只要照著拍就能獲得認可的普通商業片。雖然他說,“買了版權就大大方方地用”,但仍然在一開始就做了很多“邊界之外的選擇”。
比如,捨棄原作的秋田犬,選擇沒有經過血統固化的中華田園犬,且都是肉狗市場上救下來的。這些毫無經驗的動物演員,敏感、警覺、注意力難以集中、怕水、怕光、更怕人,是片場最難搞的“大牌”。
“buff疊滿”的後果就是,“第一場戲就受了很大打擊”“原本100分的訓練表現,現場可能只能達到25分”“殺青半個月後,還一直做噩夢”,徐昂坦誠拍攝期間的焦慮。
這位年少成名、頗具才華的青年導演,2001年中戲畢業後進入北京人藝,曾執導話劇《喜劇的憂傷》,16200張門票一張不剩,創下近20年來北京話劇票房賣座紀錄。2013年初執電影導筒,改編自美國電影的作品《十二公民》獲得羅馬國際電影節最高獎項“馬可·奧雷利奧”獎。
如今,徐昂說自己仍走在“不設界碑”的職業之路上,沿途,堅持與妥協同在,焦慮與鬆弛俱存。
以下是徐昂的自述:
“邊界之外的選擇”
我大概是2017年接到《忠犬八公》的劇本,2018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要去做一個決定——到底是用中國的訓犬團隊還是用國外的。
我們當時一開始更傾向於北美團隊,因為他們拍過的電影比較多,而且有比較成功的案例。但是後來和他們溝通,發現了一些問題。他們認為應該用他們已經訓練好的犬種,比如邊牧、拉布拉多、秋田等國外的品種犬。
當我們提到國內的大黃狗(中華田園犬),他們很陌生,也沒有經驗。如果特意培訓的話,時間成本和資金成本都更高,他們完全不理解我們為什麼一直要去選擇中華田園犬。
對我來說,選擇本土犬種並不是一個特別猶豫的事情,雖然在前期準備工作中一直有人告訴你這是在邊界之外的選擇。
它不在邊界內,是因為本土犬種有很多不可控的地方。中華田園犬是沒有經過血統固化的犬種,個體差異非常明顯。同一品種下,相似的、拍攝過程中可以互相替換工作的犬隻很少,所以要想選到形象相近的動物演員是很難的。
對犬種的堅持是我們給自己添了一個麻煩,然後這種麻煩緊接著下面的麻煩,這是沒辦法的事兒。所以當我們確定這件事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沒法用北美團隊了。
最後我們選擇了國內的一個團隊,他們先帶著大黃(影片中扮演老年八筒的動物演員)給我演了一段“死”的戲。
· 《忠犬八公》劇照。
大黃是一個“老演員”,參演過四五部電影。它最早是一條流浪狗,性格比較穩定、神經比較大條,見過很多大場面,所以它對人很多的場景也泰然自若。
但是由於它來的時候年齡比較大了,在它那個年齡段有些動作它已經開始拒絕了,就像小孩子上過初中,然後再讓你回去念 1 + 1 = 2一樣,它會覺得我不要學這個。
至於其他所有參與拍攝的小狗,都是我們在肉狗市場按斤買來的,當時是想能救下來一條是一條吧。
而且在最開始去選狗的時候就已經想好了,我們得讓這些狗有一個歸宿,就是最後拍攝完得有一個家庭來接納它。所以後面除大黃外的17只動物演員也都找到了領養家庭。
再有一個就是參與這個電影項目的人,他們都是因為喜歡狗才參與的,所以我們不希望自己見到那個場面——一幫人強制一個動物為了你的需求去幹一件事情,這是突破我們自己的標準和底線的。
“導演,我們在等什麼?”
第一場戲是八筒望江的場景,拍了整整一個晚上。畫面遠景是嘉陵江,然後八筒入鏡,坐定,望著江面,然後起身走到另一個地方左右看一下,尋找一下之後,走出畫面。
這些簡單的基礎動作開拍前都訓練過,但實拍時,你會發現狗狗的敏銳度和它的注意力會下降,尤其在初期的時候,原本100分的訓練表現,現場可能只能達到25分。這個衰減會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我認為拍攝真正意義上開始進入正軌,應該是在開機之後的大概兩到三週。
小狗們剛來的時候都是非常恐懼的,很多小狗還沒有培養出健全的性格。比如你用手給他餵食的時候,它是不接受的,也不太接受你抱它,它只要腳一離地,馬上就開始有那種焦慮,有的時候還會憤怒。
所以我們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時間。很多時候我們在片場,總是所有機器、演員都就位了,但因為狗狗不願意做動作,拍攝進行不了,就要一直等。
“導演,我們在等什麼?”每天總是不斷有人過來問我這個問題,我要一遍一遍地解釋原因。
觀眾在影片中看到的,展現人與狗之間的情感互動和交流的部分,都是經過耐心訓練的結果,通過不斷地重複讓它們不斷地脫敏,把它天性裡面的恐懼,逐漸地轉化成一種被獎勵的行為。
而訓練部分是非常瑣碎、龐雜的一個過程。比如說燈光的問題,動物演員很難適應拍攝時的強光,直視一個很亮的東西是違背它天性的。我們就要想盡辦法,比如說訓犬師拿著吃的站在燈光一側,它有可能就會往這邊關注一下,去勉強適應燈光。
表現狗狗的視線變化和心理活動也很麻煩。因為狗狗的眼睛基本上是被黑色的瞳孔佔滿的,看不出來視線的變化,所以就需要有人能給它打一點眼神光,要給它託個板。
再比如說我們倆在說話,人可以忽略周圍東西的干擾,但是狗對移動的物體非常敏感,要讓它對一個從它邊上路過的物體無感十分困難,那就需要這個東西在它的生活裡邊無數次地在周圍移動過,直到它對這個東西脫敏。
所以,有些場景我們是無數次地帶著它們不斷地去那兒熟悉環境。比如說拍狗狗來到教授家之前,我們在搭建場景時就帶著動物演員去裡邊待一會兒,看一看,讓他在那裡留一些自己的氣味。
拍八筒在站臺追火車的那場戲,我們提前兩週就讓動物演員去到現場,適應移動的火車,適應站臺周圍的環境。即使這樣,現場還是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安全問題也必須要全面考慮。
“在自己的喜歡裡邊往前活”
認真說起來的話,每一場戲都很難,沒有容易的,區別只是哪場戲你花了更多的時間,哪場戲損失了更多的內容。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你要去衡量和協調,哪些東西必須要,哪些東西可以做取捨,哪些東西要改變。因為我們沒法跟一條小狗說你做錯了,你只能說不斷去修改自己的方案,捨棄一部分你原來認為必須要達到的文學性描述。
拍攝過程中非常非常焦慮,就是你的一切努力或者說預想,在現場都有可能落空,每天都有可能。所以一直到拍完這戲,大概過了半個月,我還一直在做同樣的噩夢——今天狗狗不願意演,怎麼辦。
我必須得說,當《忠犬八公》這樣一個故事出現後,很多人與動物的故事母體都是脫胎於此,很多情感的來源是從這兒來的。你說翻拍,其實我們原來做話劇的時候,就沒有翻拍這麼一說。話劇的創作是拿全世界幾乎所有的經驗做評估,這對我們來說並不鮮見,所以我對這方面不太計較。
我其實只是在一個我自己的軌道上面往前開,然後有時候停下來,有的時候甚至倒退,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站。就像陳教授在戲裡那句臺詞,人這一輩子長了不過大幾十年,什麼叫活著?在自己的喜歡裡,那才叫活著。
我就是在自己的喜歡裡邊往前活,你很難說你還打算在哪兒立個界碑,或者怎麼樣。我覺得那不是我要乾的事。但沿途你會路過一些風景,覺得特有意思,我覺得人這一輩子就是幹這件事兒。
關注人民文娛
點一下你會更好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