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楷卓 於子軒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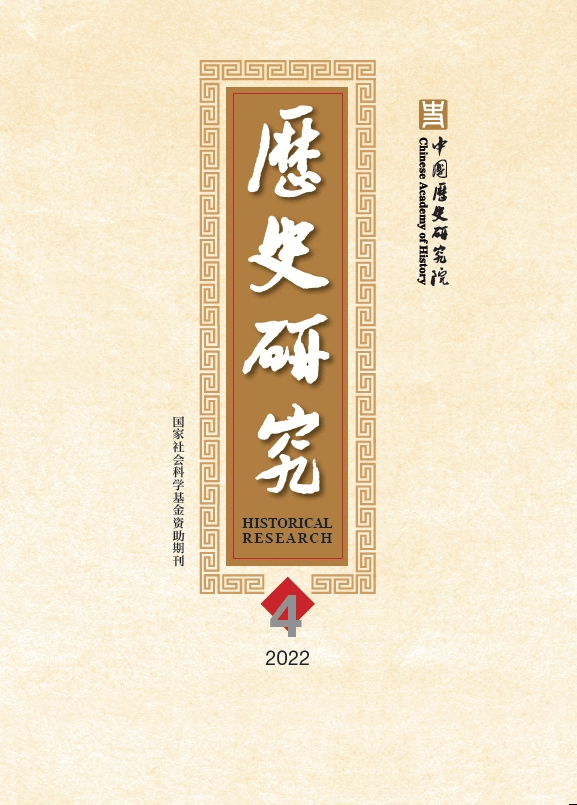
摘 要:現行突厥早期史(583年以前)的敘述框架,即土門系、室點密系突厥東西並立說,建立在沙畹對諸種語文文獻的錯誤統合之上。突厥早期史史料可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同時代形成的文本;二是後世突厥人的歷史記憶;三是以《新唐書·西突厥傳》為代表的後世史家的重構。史料批判的結果表明,室點密既不是活躍於突厥西部的Silzibul/Sizabul/Sinjibū,也不是征服西域自立為可汗的西突厥汗國始祖;“泥利國書”中與另一位可汗一同擊敗柔然的室點密形象則相對可靠。對突厥汗國西部早期歷史的考察顯示,汗國早期政治結構並非東西並立,而是大可汗獨尊於上。
關鍵詞:突厥 室點密 《新唐書》歷史記憶 史料批判
相較於中原定居社會的歷史,北方民族史研究的首要障礙是史料匱乏和分散。為此,前輩學者在諸種語文的傳世和出土文獻中,努力搜尋與北方民族史有關的片段,儘量填補原有歷史敘述的空白。然而,與發掘新出土或過去未被注意的史料相比,以往學者在檢討史料來源、層次和可靠性等方面投入的精力還相當有限。史料是在特定情形下、由特定作者因特定目的為特定讀者寫下的,即使它們之間沒有明顯矛盾,也不應秉持“拿來就用”的態度。苗潤博呼籲對史料做“加法”的同時,也需要適當考慮做“減法”。他對契丹早期史的個案研究表明,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契丹早期史實際上是三重濾鏡之下的圖景。與此相似,突厥早期史史料也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同時代形成的各種語文文本,二是以各種形式保存至今的後世突厥人的歷史記憶,三是後世史家以線性思維對既有史料中模糊不清的內容進行的重構。想要接近突厥早期史的本相,必須“層層剝離”,首先釐清後世史家的重構,然後分析後世突厥人的歷史記憶,最後結合同時代形成的文本重審突厥早期史。
若以隋開皇五年(585)突厥沙缽略可汗向隋朝稱臣時所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為準,那麼作為政治體的突厥,其歷史可以上溯至530年前後。在這之後,突厥從阿爾泰山腳下的小型部落發展成雄踞北方草原的龐大汗國。然而,開皇三年,曾於爭議中取得大可汗之位的沙缽略可汗,與木杆可汗之子阿波可汗相互攻擊,後者是不久前去世的他缽大可汗指定的汗位繼承人。這場戰爭致使突厥汗國內部出現兩位大可汗,從而揭開突厥動亂與分裂的序幕。本文關注的突厥早期史,即指自530年左右突厥政治體形成到583年突厥走向分裂之間的歷史時段。
自沙畹名著《西突厥史料》以降,突厥早期史討論最多、最核心的問題,是突厥汗國內部所謂“東西分立”問題,即被認為開拓並統治突厥汗國西部廣袤疆域的室點密可汗、後來統治這一地區的達頭可汗,與以蒙古高原為中心的土門系可汗的關係問題。沙畹的以下觀點被學界廣泛接受:漢文史料中的室點密可汗、古突厥文碑銘中的Ištämi Qaγan,就是阿拉伯文史料中擊敗嚈噠的Sinjibū Khāqān、希臘文史料中通使拜占庭的Silzibul/Sizabul;他是突厥汗國建立者土門可汗的弟弟,雖然不是名義上的大可汗,但實際統治突厥汗國的西部地區;後來的西面可汗達頭即希臘文史料中的Tardu,是室點密可汗的兒子,他的許多後代成為西突厥汗國的可汗。
然而,這一整套敘事得以成立的基礎,是後世史家重構的世系、被故意製造的先祖記憶以及誤讀希臘文史料導致的草率勘同。沙畹首先不加懷疑地接受僅見於《新唐書·突厥傳下·西突厥》(下文簡稱“《新唐書·西突厥傳》”)的突厥早期世系: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
根據這個世系,室點密是土門之弟、達頭之父。然後,沙畹又不加懷疑地接受《舊唐書·突厥傳下》中一段反映阿史那彌射先祖記憶的文本(下文稱“《彌射傳》”):
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從單于統領十大首領,有兵十萬眾,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為可汗,號十姓部落,世統其眾。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貞觀六年,詔遣鴻臚少卿劉善因就蕃立為奚利邲咄陸可汗……
據此,室點密曾向西開疆拓土。沙畹又聲稱,從彌南德《歷史》(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中可分析出Tardu是Silzibul之子,因為其中提到Tardu 是Silzibul之子Turxanthus的“同父異母兄弟”(frère consanguin)。因此,Silzibul 就是向西開疆拓土的室點密。沙畹還從審音勘同的角度,提出Silzibul/Sizabul 的後半部分zibul/zabul 對應Yabγu(葉護),這正符合《舊唐書·突厥傳》中所說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
然而,即使不考慮兩段漢文史料的可靠性問題,將Silzibul與室點密勘同也是錯誤的。沙畹理解成“同父異母兄弟”的希臘語詞omaimon其實有兄弟、親戚和同族等多種含義,通常泛指有血緣和親族關係的人。塞諾正確指出,“不把Silzibul與室點密等同起來是明智的”。沙畹這個勘同的另一個基礎——室點密有“葉護”名號,也不正確。前引《舊唐書·突厥傳下》中“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 漢文文獻中“在本蕃”往往用於入唐蕃人,並且下一句又稱唐廷冊立其為可汗,因此這裡說的絕不是室點密而是彌射。更關鍵的兩個證據是,這句話在更早的《通典》中作“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而在晚出但史源相同的《新唐書·西突厥傳》中作“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為莫賀咄葉護”。因此,沒有史料表明室點密有“葉護”名號。另一方面,zibul/zabul與yabγu第二個音節差別很大,將二者勘同比較粗糙。從希臘文文本所記人物關係、漢文文本所記室點密名號、審音勘同三個角度看,Silzibul與室點密完全不能勘同。
塞諾雖然反對這個勘同,但未意識到,除了這個勘同以外,現有敘事中室點密的世系和事蹟賴以成立的兩條漢文史料同樣靠不住。懷疑這兩條史料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在突厥汗國早期形成的任何語文的史料中都找不到室點密的蹤跡。重審突厥汗國早期史,必須首先理清相關史料的層次。
第一層,同時代形成的各種語文的文本。突厥汗國分裂以前形成的文本中,唯一反映突厥汗國官方立場的是《布古特碑》。作為突厥早期史的一手文獻,該碑是他缽可汗死後(580)建立的,追記了木杆、他缽兩可汗的統治,記錄了他缽可汗的葬禮和庵羅可汗的即位。以彌南德《歷史》為代表的希臘文文獻、以塔巴里《歷代先知與帝王史》(Tārīkh al-rusul wa al -mulūk)為代表的伊斯蘭史料、以《周書》《隋書》為代表的漢文文獻,都是後來經過一次或多次傳抄才最終呈現在研究者面前的。
彌南德《歷史》成書於莫里斯(Maurice)皇帝執政期間(582—602),主要記錄557/558—582年拜占庭的對外關係。該書史源主要是檔案文件和口頭報告,其中與突厥有關的部分應完全來自拜占庭的官方檔案,真實生動地反映了突厥使者在拜占庭的言談舉止和拜占庭使者在突厥的所見所聞。此外,還有一些旁見側出的希臘文史料提到了早期突厥,例如阿加塞阿斯(Agathias Scholasticus)《歷史》(Histories)、厄瓦格利烏斯(Evagrius
Scholasticus)《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等。
伊斯蘭史料中與早期突厥有關的部分集中於對突厥擊敗嚈噠、威脅波斯的記述,分見於迪納瓦里(al-Dīnawarī)《長史》(Kitāb al-akhbār al-ṭiwāl)、塔巴里《歷代先知與帝王史》、薩阿利比(al-Tha’ālibī)《知識妙語》(Laṭā’if al-ma‘ārif)等十餘種9—13世紀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獻。這些記述的史源主要是薩珊波斯時代的中古伊朗語材料,它們最初很可能來自親歷與突厥和戰的薩珊波斯統治階層。伊斯蘭史料中相關內容經詳細對勘後,很多被證實是可靠的,可以追溯到突厥早期時代。
漢文傳世文獻對突厥早期史的記錄最為詳盡,《周書》《隋書》雖成書於唐初,但史源主要是周隋時代的官方檔案和官方史籍,“原始性”很強。因此,兩書與早期突厥有關的內容史料價值極高,尤以《周書·突厥傳》《隋書·突厥傳》《隋書·長孫晟傳》為大宗。同時成書的《北齊書》雖無突厥專傳,但有一些史料與突厥有關。後出的《北史》《通典》《冊府元龜》《太平寰宇記》《資治通鑑》(下文簡稱“《通鑑》”)等書有關早期突厥的部分,基本不超出《周書》《北齊書》《隋書》所載。除此之外,隋代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唐初道宣《續高僧傳》等佛教典籍中有一些涉及早期突厥的材料。漢文石刻史料中有不少與突厥早期史有關。吐魯番出土文書中也有一些反映了突厥對麴氏高昌的影響,不過涉及早期突厥的不多。
第二層,以各種形式保存至今的後世突厥人的歷史記憶。依文本形成的時間順序,包括泥利可汗(595—604年在位)及其子對突厥早期史的敘述、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記憶和突厥第二汗國對突厥早期史的官方記憶。前者分見於希臘文的泰奧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歷史》(History of Theophylact Simocatta)中轉述的“泥利國書”(595)和粟特文的小洪納海石人(Mongolküre inscription,604)。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記憶零星見於漢文傳世文獻,如前引《舊唐書·突厥傳》阿史那彌射部分、《元和姓纂》史氏“河南”望條等;更多見於入唐突厥人墓誌,其中重要者如《史善應墓誌》(643)、《李思摩墓誌》(647)、《阿史那懷道墓誌》(727)等。突厥第二汗國對突厥早期史的官方記憶見於鄂爾渾古突厥文碑銘,即《闕特勤碑》(732)和《毗伽可汗碑》(735)古突厥文部分。
第三層,後世史家以線性思維對既有史料中模糊不清的內容進行的重構。確切地說,這些重構不能算作史料,而是古代學者的突厥史研究,集中體現於宋祁所修《新唐書·西突厥傳》,其中涉及早期突厥和西突厥的世系,完全不見於目前所見其他任何傳世和出土文獻,基本上是宋祁的重構。
沙畹依據的《新唐書·西突厥傳》不見於他書的突厥早期世系,是宋祁的主觀臆測。許多學者已指出,《新唐書》列傳特別是“四裔傳”的文本在可靠性上存在諸多問題,問題突出的,比如《回鶻傳》前半部分被認為不能作為歷史學考察的依據。《突厥傳》也存在類似問題,《通鑑》編者就對該傳的史料價值持消極態度。該傳所附《西突厥傳》亦不例外,它所記載的西突厥汗國世系有嚴重問題。
由於西突厥汗國滅亡時間較早,其末代可汗阿史那賀魯降唐後不久便去世,因此西突厥汗國曆史的漢文版本很早就成型於唐朝官修實錄、國史之中。這塑造了相關史源的單一面貌,《通典》《舊唐書》《冊府元龜》《通鑑》等對西突厥王族世系的記載保持了驚人的一致性。再者,由於唐朝對西突厥汗位更替有間接或直接的干預,許敬宗等國史修撰者又是這一歷史的親歷者,因此唐朝國史對西突厥可汗世系的記載應是準確可靠的。然而《新唐書·西突厥傳》有兩處記載與他書所記完全不同。
一是西突厥末代可汗阿史那賀魯的身世問題。唐朝對投降者賀魯的身世背景必然相當瞭解。源自國史的《通典》《舊唐書》等書對賀魯身世的記載完全相同,都稱其是“曳步利設射匱特勤之子”,唯有《新唐書·西突厥傳》於“曳步利設”之前多出了“室點蜜可汗五世孫”八字。賀魯與室點密的關係在現存史料中僅見於此,但宋祁不太可能掌握《通鑑》等其他史籍作者見不到的材料。諸書皆記阿史那彌射與阿史那步真為族兄弟,但從未言及賀魯與前兩人的關係,因此不能由《通典》《舊唐書》稱彌射為室點密五代孫,推定賀魯是室點密五世孫。宋祁恐怕就是作出這樣的推定,才製造了上述世系。
二是關於《新唐書·西突厥傳》所謂“泥孰系”可汗世系問題。其他同源文獻所提供的相關世系與此有所不同(見圖1、2):
對比兩份世系,可以發現《新唐書·西突厥傳》有兩處不同於其他史籍。其一,他書皆記乙毗沙缽羅葉護可汗的父親,即“伽那(設)”是泥孰可汗和咥利失可汗的弟弟,而《新唐書》卻將泥孰可汗與伽那設記作同一人。學界普遍認為,宋祁此處所記有誤,應以他書記載為確。其二,《新唐書》與他書對乙毗射匱可汗父親的記載有所不同。他書皆記作莫賀咄乙毗可汗,並未明確指出這位可汗的世系情況。而《新唐書》給出的是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並多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為咥利失可汗之子並繼承汗位的記載。有學者認為,雖然乙屈利失乙毗可汗為咥利失之子並繼承汗位一事僅見於《新唐書》,但是《新唐書》增補必有所據。然而,就西突厥汗國曆史而言,諸書所據可靠史料基本相同,《新唐書》並無優於他書之處。掌握《新唐書·西突厥傳》所用史料並於修撰時遍覽諸書的司馬光等人,沒有理睬《新唐書》這一獨有記載,而是直接遵從唐朝國史等史料的記錄。《新唐書》的說法其實是宋祁錯誤研究的結果。
學界普遍認為,《新唐書》所記乙屈利失乙毗可汗就是他書所記莫賀咄乙毗可汗,因為二者都是唐太宗遣使冊封的乙毗射匱可汗之父。但受《新唐書》給出的世系影響,學者以往或沒有意識到、或否認這個人就是殺死統葉護自立的那位諸書記為莫賀咄俟屈利毗、莫賀咄侯屈利俟毗、莫賀咄俟屈利俟毗或莫賀咄屈利俟毗的可汗。儘管各有訛字或脫字,但“俟”訛為“侯”、“俟”與“乙”音譯同一個非漢語音節都是極為常見的現象。漢字轉寫古突厥語,“失”、“施”等字常常省去;當然,從古突厥語的角度看,“乙屈利失乙毗”中的“失”更可能是衍文,因為“屈利”(küli)、“乙毗”(*elbär?)都是常見的突厥名號。因此,《新唐書》所記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他書所記莫賀咄乙毗可汗,諸書所記殺死統葉護自立的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莫賀咄侯屈利俟毗可汗、莫賀咄俟屈利俟毗可汗或莫賀咄屈利俟毗可汗無疑是同一人,他的完整可汗號可復原為莫賀咄俟屈利俟毗(*baγatur el küli elbär),即宋本《冊府元龜》中的形式。當溫無隱奉命來到西突厥冊立“突厥可汗子孫賢者”乙毗射匱可汗時,得知其父親的可汗號是“莫賀咄乙屈利失乙毗”, 這個漢字譯寫形式與十幾年前譯寫的“莫賀咄俟屈利俟毗”稍有不同。後來“莫賀咄乙屈利失乙毗”在《新唐書》中被省作“乙屈利失乙毗”,在他書中被省作“莫賀咄乙毗”。
從源自國史的《通典》等書未對乙毗射匱可汗之父作常規背景介紹來看,許敬宗等唐朝史官很清楚這裡的莫賀咄乙屈利失乙毗,就是之前提及的莫賀咄俟屈利俟毗。然而,缺乏古突厥語知識並且不是歷史親歷者的宋祁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何時在位,就成了他沒有材料解決卻又極力試圖解決的問題。在宋祁看來,泥孰即伽那(設),則咥利失可汗是莫賀設僅有的另一個兒子,沒有材料記錄他的後代。並且,乙屈利失乙毗可汗及其子乙毗射匱可汗孤懸於這個世系之外。宋祁以線性思維將兩者強行拼接到一起,就有了《新唐書》脫出於他書的那一句:“國人立其(即咥利失——引者注)子,是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逾年死。”這當然是錯誤的,莫賀咄俟屈利俟毗可汗(即乙屈利失乙毗可汗)是莫賀設的伯父或哥哥,而不是莫賀設的孫子。現代學者不加批判地將宋祁的研究成果視為史料,就不得不面對兩種相互矛盾的西突厥可汗世系。
就西突厥汗國曆史而言,宋祁掌握了完備的唐朝官方史料,卻依然交出了不合格的“答卷”。面對突厥早期史,宋祁掌握的原始材料更為有限,主要是今天仍能見到的《周書》《隋書》。然而《新唐書·西突厥傳》中的突厥早期世系卻與《周書》《隋書》的記載有所不同,只能是宋祁的研究所得。畢竟,比《新唐書·西突厥傳》掌握了更多可靠史料的《通典》和蒐集史料更全面、考訂史事更嚴謹的《通鑑》並沒有這些內容。
《周書》《隋書》所記多種不同版本的突厥起源傳說和早期世系,在《新唐書·西突厥傳》中卻變成單一且清晰的版本(見圖3):
這份世系中土門、室點密兄弟以前的譜系,是糅合《周書·突厥傳》《隋書·突厥傳》兩個毫不相干的突厥起源傳說而成(見圖4、5):
圖4 《周書·突厥傳》“索國說”所載突厥早期世系A
圖5 《隋書·突厥傳》“西海說”所載突厥早期世系B
宋祁將屬於不同版本的A與B統合在一起,意味著他相信突厥只有一種起源,多種起源故事不過是對同一歷史的不同表述,因此只需將其中傳說色彩較淡的內容組合在一起,就能得到真實且唯一的突厥起源歷史。站在宋祁的視角,只要著眼於“狼所生”、“居某某山”、“阿賢設”三個要素,並忽略人物世系的模糊之處,我們的確能把譜系A、B 統合為一個版本(見圖6):
最後,去掉時代較早的訥都六父祖,刪去相互衝突的阿賢設(阿史那),再將大葉護與某種今天已看不到的材料中的突厥先祖“吐務”勘同,就得到了《新唐書·西突厥傳》所記突厥早期世系的前半部分。總而言之,《新唐書·西突厥傳》所記土門、室點密兄弟以前的世系完全出自宋祁的重構。
上述表明,宋祁在編纂《新唐書·西突厥傳》時,是以線性思維將突厥可汗世系中相對模糊的部分重構為清晰明確的版本。我們有理由將《新唐書·西突厥傳》視作突厥史史料纂集和研究的融合體,對其記載可靠性保持警惕。畢竟,關於6—7世紀發生的史事、7—8世紀詳細的記述中完全沒有提及的內容,突然出現在11世紀的史料裡,現代史家絕不能輕易相信。因而不難看出,宋祁關於土門和室點密是兄弟、室點密和達頭是父子的記載,極有可能是一項歷史發明。畢竟,這些內容在以《周書》《隋書》《通典》為代表的北周、隋、唐史料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也沒有被掌握《新唐書》史源的《通鑑》提到。特別是就突厥早期史而言,上述漢文文獻又以《周書》《隋書》的史源最為原始,它們卻完全沒有提到室點密其人。這一反常情況在《隋書·西突厥傳》中體現得尤為明顯——隋朝通曉西域諸事的裴矩向隋煬帝介紹達頭可汗的孫子:“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倘若室點密真的是土門的弟弟、達頭的父親,並且如《新唐書》所言是一位可汗的話,裴矩為什麼不繼續追溯至這位室點密可汗呢?無疑說明,《新唐書·西突厥傳》的這些內容並非史實。
宋祁應該是將《隋書》關於達頭可汗“舊為西面可汗”、射匱家族“世為可汗,君臨西面”的記載,與《通典》《舊唐書》關於室點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為可汗,號十姓部落”的記載結合起來,得出室點密是達頭父親的結論。隨後,考慮到達頭是沙缽略的叔父,而沙缽略是土門的孫子,他進而認定室點密是土門的弟弟。宋祁還注意到一份關於“瑟帝米”的材料,根據內容可以將“瑟帝米”與室點密勘同——這份材料或許與下文討論的把室點密記作“室德媚”的《阿史那懷道墓誌》一樣,反映的是入唐突厥人制造的歷史記憶。於是,《新唐書·西突厥傳》中土門、室點密和達頭三人的關係,就這樣被建構出來。
室點密完全不見於第一層史料,但多次出現在第二層史料即後世突厥人的歷史記憶中。突厥第一、第二汗國的官方歷史記憶和某些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記憶中,都能找到室點密的蹤跡。泰奧菲拉克特·西摩卡塔《歷史》成書於7世紀上半葉,其中一段涉及突厥的文本,轉述自6世紀末一位突厥可汗致莫里斯皇帝的國書,過去學界一直將這位突厥可汗比定為達頭,然而此比定存在很多難解之處:拜占庭方面既然早在576年就知道了達頭可汗,為何此處不說明送來國書的可汗名號?達頭可汗掌權已十餘年之久,為何偏偏此時遣使拜占庭,宣佈自己的勝利?
近年來,魏義天在突厥史和拜占庭史最新研究的基礎上,重新為這封轉述的國書作了詳細箋註,終於給出符合歷史背景的解讀。根據《歷史》上下文推知的國書送達拜占庭的年代,與小洪納海石人提供的泥利可汗即位年代恰好相符,都是595年;此外,國書中描述的敵我形勢也表明國書代表泥利可汗的立場,內容則是泥利可汗對突厥第一汗國史的官方歷史書寫。“泥利國書”中敘述的突厥第一汗國史,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可汗擊敗了嚈噠(Abdeli/Hephthalite)國的首領,征服了他,奪取了該國的統治。
(2)可汗與室點密可汗(Stembis Chagan )聯合,征服了柔然(Avar)…… 柔然被打敗後,一些人逃到了中國(Taugast),另一些柔然人……來到了高句麗(Mucri)。
(3)然後可汗……征服了全部的烏古爾人(Ogur)。
(4)烏古爾人被完全擊敗後,可汗劍鋒直指Kolch國的統治者。
(5)正當勝利向可汗光榮地微笑時,突厥人陷入了內戰。
(6)許多殺戮過後,可汗重新成為他自己土地的主人。
阿瓦爾與柔然的關係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話題,本文不打算涉及。但無論如何,根據被擊敗後逃到中國和高句麗的說法,(2)中所謂Avar無疑指柔然。整段敘述除顛倒突厥征服柔然和嚈噠的順序外,完全符合東西方史料所見550—595年突厥第一汗國史的基本框架,而這個顛倒是泰奧菲拉克特·西摩卡塔錯誤調整轉述順序的結果。從希臘文文本來看,近50年的史事都圍繞泥利可汗展開,這當然不符合事實,可能是泥利可汗有意誇大其詞,也可能是國書翻譯或轉述過程中丟失了不同可汗的名號所致。在這份文本所反映的突厥第一汗國官方歷史記憶中,(2)對應的是土門時期的歷史,(1)(3)(4)對應的是泥利祖父木杆的事蹟。室點密可汗只出現在(2)中,他與大可汗一起征服了柔然,並沒有參與後來向西征服嚈噠、烏古爾等戰爭;沒有提到他與其他可汗的關係,希臘人也沒有將他與幾十年前遣使拜占庭的Silzibul 聯繫起來。595年上距室點密的時代不過兩代人時間,對泥利可汗來說,室點密的事蹟一定是親歷過的長輩在他童年時代就經常提起的故事,這個歷史記憶是相對清晰的。因此,“泥利國書”中的室點密形象是現存所有時代所有語文史料中最接近歷史現場的一個,史料價值遠勝7—8 世紀至少四五代以後突厥人的歷史記憶,可惜此前並未得到學界重視。
突厥第二汗國的官方歷史記憶中也有室點密,雖然相對模糊,但竟與“泥利國書”中的室點密形象大體相似。《闕特勤碑》古突厥文部分開頭追記突厥第一汗國曆史說:
……在人類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Bum.n)可汗和室點密(Ištemi)可汗。他們成為可汗後……率軍征戰,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全都征服了(他們)。他們使有頭的頓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他們讓人們住在東方直到大興安嶺(Qadïrqan yïš),西方直到鐵門(Tämir qapïγ)的地方……他們之後去世了……
在此,室點密可汗是突厥建國的兩個大人物之一,他們一起東征西討,似乎差不多同時去世。由於年代久遠,記憶變得模糊,當時的突厥人將突厥建國和對外征服的全部功績都歸於最初的兩位可汗,全然不提木杆,顯然是把“泥利國書”(1)(3)(4)部分內容混入(2)中。因此,突厥第二汗國官方記憶中的室點密形象與第一汗國時期“泥利國書”中的室點密形象本質上是一致的:室點密作為與另一位可汗(布民)對等的可汗活躍於突厥擊敗柔然的戰爭中;既然通常被比定為土門的布民可汗事實上還沒徹底擊敗柔然就死了,與布民可汗並肩作戰的室點密,應當差不多同時退出歷史舞臺。在完全沒有第一層史料的情況下,目前只能根據突厥第一、第二汗國官方歷史記憶復原出這樣一個室點密形象。
在以上兩個官方記憶之間,漢文史料保存的兩個入唐突厥人的家族記憶與室點密有關。上引《通典》《舊唐書》所載《彌射傳》中的室點密事蹟過去常被視作信史,因此成為現行突厥早期史框架的重要基礎。但是學界對於這一重要文本的認識,值得重新審視。首先要明確該文本的屬性。從“單于”一詞的用法出發,筆者認為該文本應當源自一份以彌射生平為中心並帶有文學色彩的傳記類文獻。這份文獻通過唐朝史官之手進入國史《突厥傳》中,後來又分別被《通典》和《舊唐書》保存下來。從當時傳記類文獻的寫作體例和唐朝國史中人物傳記的修撰過程來看,敘述了室點密事蹟的文獻應當是彌射後人呈交給史館的“彌射行狀”。其次需要考量文本內容的可靠性。松田壽男從“單于”、“十姓部落”等用詞出發,判斷該文本“完全帶有傳說的意味”,是在貞觀中西突厥實行十姓制之後才被製造出來的傳說,這一看法不無道理。除此之外,還應該注意到唐朝史料對彌射身世記載存在著結構性缺漏的情況。遍覽唐朝史官編纂的西突厥史料,可以發現唐人總是直接或間接地揭示每位可汗的父祖信息,然而對彌射父祖的記載卻是一片空白。考慮到彌射家族在相當長時間裡,是唐朝經營西突厥故土的重要政治旗幟,這一缺漏顯得很不尋常。
1993年出土的《阿史那懷道墓誌》(下文簡稱“《懷道墓誌》”)也挑戰著《彌射傳》相關敘述的可靠性,《懷道墓誌》載:
可汗諱懷道……五代祖室德媚可汗,鷹揚雲中,虎據天外。橫行者五十萬眾,厥角者卅六蕃。曾王父閼氏葉護……大父諱步真,號咄六葉護……貞觀中入朝……列考曰斛琴(瑟)羅……冊竭忠事主可汗……自麟德之始,洎開元之中,出入五朝,回覆萬里……歷官廿又七政,享年一百一十有九歲。可汗……開元十五年……薨……春秋五十有七。
在《懷道墓誌》中,室點密是懷道的高祖;在《彌射傳》中,室點密也是彌射高祖。兩者都以室點密作為中心人物的高祖,顯然是受到華夏譜系書寫格套的影響而被製造出來的。考慮到彌射與步真的族兄弟關係,《彌射傳》稱彌射是室點密玄孫,與《懷道墓誌》稱步真是室點密孫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此外,《懷道墓誌》還存在兩處硬傷。其一,按志文,斛瑟羅出生於600年左右,640年隨父步真入唐,直到麟德元年(664)方入仕為官,此時已年近70歲,有悖常理。寫作者想必是將步真的生年置於斛瑟羅頭上,才製造出如此離譜的敘事。其二,一個突厥男性貴族使用“閼氏”這一匈奴最高統治者妻子的名號作為自己的官號,實在匪夷所思。室點密與步真只隔一代,顯然不合理;“閼氏”即便置換為“可敦”,也不應當被突厥男性貴族使用,意味著步真家族對步真父祖的記載是錯誤的,甚至是在故意隱瞞。無疑說明,上述兩個與室點密有關的世系都不可靠。
那麼,彌射和步真家族為什麼要構建一個征服西域的室點密形象呢?筆者認為,這個形象的兩個要素“室點密”和“征服西域”應拆開分析。《彌射傳》和《懷道墓誌》既沒有提到土門或木杆,也沒有提到達頭,意味著他們與西突厥汗國的兩大統治家族沒有直接關係,屬於阿史那氏的偏遠支系。對唐朝來說,土門系和達頭系的世系是清楚的,那麼在突厥人的歷史記憶中,相當重要但事蹟和世系均不清晰的室點密自然成為攀附的最佳選擇。彌射、步真二人被唐朝冊立為可汗鎮撫西突厥餘部,那麼宣稱先祖曾征服西域、“號十姓部落,世統其眾”,自然滿足了唐朝經營西域的政治需要。因此《彌射傳》和《懷道墓誌》中的室點密事蹟不應被視作信史,遠不如“泥利國書”和《闕特勤碑》中的室點密形象可靠。進一步證實這一點,需要圍繞第一層史料重新審視突厥早期史的框架。
過去,國內學界對突厥汗國早期政治結構雖有不同看法,但基本建立在對不同層次漢文史料的混用、沙畹對西方史料的轉述以及他對東西方史料統合的基礎之上。現在,我們有機會以同時代形成的各種語文文獻為基礎,重建突厥早期史的基本框架。這項工作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認識突厥汗國西部的政治結構。
活躍於突厥西部的第一位強力人物,是558年之前出現在波斯人視野中的Silzibul/Sizabul/Sinjibū,他是559—560年突厥滅亡嚈噠的直接負責人、568—569 年遣使拜占庭的突厥可汗。他的汗庭,據570年抵達該處的拜占庭使者報告,是在白山(Ektag)附近群山環抱的山谷中,即裕勒都斯河谷或特克斯河谷。BSilzibul 無疑是突厥西部的實際控制者,但是學界對他在汗國內部地位的認識,一直以來掩蓋在“室點密”的迷霧之下。要解答這一問題,必須重視《續高僧傳·釋道判傳》所保存的一則史料。釋道判於北周保定四年(564)出發,欲往印度探求佛法;他先到達高昌,“又請國書,至西面可汗所”,但是卻在此處受阻,幸虧得到北周使者相助,才得以脫身。從釋道判在高昌順利取得國書一事看,他在離開高昌後一定是按計劃向西前進,才抵達“西面可汗所”。那麼此處的西面可汗指的是誰呢?學界以往將之比定為室點密(Silzibul)。從高昌距離Silzibul汗庭不遠來看,這位西面可汗的確是Silzibul,但不應將之與室點密聯繫起來。
過去人們相信Silzibul即室點密、室點密系突厥事實上獨立於土門系突厥,因此認為漢文史料所記土門系大可汗下屬的東面、東方、西方小可汗,不能與室點密系西面可汗相提並論。這一觀點的主要根基——Silzibul是室點密,屬於錯誤勘同,已無須多言。該觀點的另一理由,即漢文史料對突厥西方、西面可汗有嚴格的區分。此說並無依據,因為古漢語中兩詞同義,而古突厥語並無方、面之分,並且西方可汗與西面可汗有別之事並無確證。因此,我們只能承認Silzibul的西面可汗身份,與木杆時代地頭可汗、他缽時代爾伏可汗的東面可汗身份和他缽時代步離可汗的西方可汗身份,別無二致。另外兩條關鍵證據是《釋道判傳》提到的西面可汗接待北周使者一事,和《周書·嚈噠傳》所記嚈噠與西魏北周的多次外交往來,尤其是北周明帝二年(558)那次。以往學者認為Silzibul遠在西域,因此西魏北周等中原王朝並不知曉突厥西部的情況,然而兩條證據無疑推翻了這一假設。既然如此,我們必須特別重視這一時期形成的東方史料:
(木杆555年滅亡柔然後——引者注)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並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周書·突厥傳》)
突厥大伊尼溫木汗(杆)……跨蔥嶺之酋豪,靡不從化;逾天山之君長,鹹皆賓屬。(《京城突厥寺碑》)
神明一般的木杆可汗(mwx’n x’γ’n)和神明一般的莫何他缽可汗(mγ’ t’t(p)[’r] x’γ’n)成了從東到西整個世界的統治者。(《布古特碑》)
上述史料都是當時人記當時事,並且包含了“我者”、“他者”雙重視角。這些最為可靠的記載,將突厥對嚈噠等國的征服歸於木杆可汗名下,認為他和繼任者他缽可汗有效控制了這一龐大汗國。我們必須承認,在他缽可汗去世以前,沒有什麼突厥首領是獨立於大可汗之外的,Silzibul同樣不例外。那麼西面可汗Silzibul的名號,是否曾在漢文史料中留下蹤跡呢?《周書·楊忠傳》記載保定三年北周聯合突厥進攻北齊一事,稱:“突厥木杆可汗控也(地)頭可汗、步雖(離)可汗等,以十萬騎來會。”地頭可汗是當時的東面可汗,擁有單獨與周邊政權開展外交的權力,在突厥汗國內部享有不小的自主權,那麼與他一同被提及的步離可汗想必也是一位重要人物。“步離”(*bɔʰ-liə̆ /li)極有可能對應希臘文轉寫Silzibul/Sizabul的最後一個音節bul。阿拉伯文轉寫Sinjibū經歷的轉譯、傳抄鏈條更長,可靠性不及希臘文轉寫;並且許多抄本中 Sinjibū詞尾有一個 alif(ا),有可能是 lam(ل)的訛寫,因此阿拉伯文轉寫的最後一個音節很可能也是būl。這意味著西面可汗Silzibul與木杆時代的步離可汗很可能是同一人。
初步理清突厥汗國內部政治結構後,我們還需要對突厥西部早期歷史作重新梳理。一是關於Silzibul西面可汗一職的任期問題。他缽可汗即位後(571),任命自己的侄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與新的東面可汗(爾伏可汗)相對。意味著他缽任命的步離可汗取代Silzibul成為新的西面可汗。這在西方史料中可以得到佐證,彌南德《歷史》的記載表明Silzibul的地位似乎下降了:當Valentinus第二次代表拜占庭皇帝出使突厥時(576年春),Turxanthus繼承了剛剛去世的Silzibul的領地和財產,而他只是眾多突厥首領中的一個,Silzibul死前的駐地更靠近突厥西境,而不是570年的Ektag/Ektel,後者已歸屬Tardu。無論是身為西面可汗時,還是卸任西面可汗之後,Silzibul都表現出能夠直接與拜占庭開展外交和軍事行動的權勢,甚至他的兒子Turxanthus也能做到這一點。這在突厥汗國曆史中並不罕見,因為後來西突厥汗國的小可汗Ziebel也有類似表現:Ziebel活躍在西突厥汗國西部,直接與拜占庭皇帝打交道,兩者甚至存在聯姻關係;Ziebel與拜占庭的同盟,使後者取得對薩珊波斯的決定性勝利;然而Ziebel只是統葉護可汗之下的小可汗。
二是彌南德《歷史》中Valentinus特別去見的Tardu,與《隋書》中“舊為西面可汗”的達頭應為同一人,他是沙缽略可汗的叔父。他應當在Valentinus到訪之前頂替他缽任命的步離可汗,成為新的西面可汗。就達頭可汗與Silzibul的關係而言,彌南德《歷史》中解釋達頭可汗與Silzibul兒子Turxanthus關係的希臘語詞omaimon,以往被草率地理解為“異母兄弟”,其實omaimon極有可能是拜占庭使團對突厥語詞äči(意為同父兄、從父兄或諸父)的翻譯。從Turxanthus而非達頭舉辦了Silzibul的葬禮,並且達頭根本沒有出席這場葬禮來看,達頭絕非Silzibul的兒子。
突厥早期已知的西面可汗有Silzibul、他缽時代的步離可汗和達頭可汗三人,他們都不是室點密。如此看來,《彌射傳》和《懷道墓誌》中的室點密顯然無法融入突厥汗國早期歷史框架之中。相較之下,時代最接近突厥建國的“泥利國書”更為可信,它所記載的Stembis Chagan是與另一位可汗攜手征服柔然的突厥祖先,並且沒有參與突厥汗國後來的對外戰爭。如果這樣的室點密真實存在的話,他應當在征服柔然之時或之後不久便死去,才會使同時代的“他者”沒有注意到其存在。
在木杆可汗和繼承者他缽可汗統治時期,突厥汗國無疑是統一且穩定的,大可汗通過任命東西兩面小可汗來掌控整個汗國。但是這種局面隨著他缽可汗的去世被打破,土門可汗的孫輩中沒有能夠掌控全局的人物,最終繼位的沙缽略可汗對汗國的控制能力明顯下降。這一情況帶來兩個變化。其一,原本大可汗任命東西面小可汗統管汗國的制度不再實施。從長孫晟的報告看,當時統治突厥汗國東部的處羅侯和庵羅並非東面可汗而是突利設和第二可汗;牙帳設在裕勒都斯河谷的達頭可汗,也被《隋書》稱作“舊為西面可汗”。其二,在沙缽略可汗統治初期,突厥陸續出現一些新的小可汗,比如第二可汗庵羅、阿波可汗大邏便、潘那可汗、貪汗可汗等。一方面,小可汗的出現反映了突厥政治的分化傾向,汗國內部矛盾重重,“攝圖(即沙缽略——引者注)、玷厥(即達頭——引者注)、阿波、突利等叔侄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另一方面,隨著沙缽略可汗控制力的下降,他自身的實力反而低於曾經的西面可汗達頭,“玷厥之於攝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這一切都為突厥汗國的分裂埋下了伏筆。
學者以往對突厥汗國的分裂,特別是對分裂時間、過程以及西突厥汗國建立問題,雖有多種不同看法,但大多是從血統入手,討論室點密系與土門系、阿波系與達頭系之間的關係,這些觀點無不根基於學界對突厥早期政治結構的瞭解。現在我們認識到,突厥早期政治結構並非東西並立,而是大可汗獨尊於上,因此對突厥汗國分裂過程的認識,不應當從東西兩部著眼,而應圍繞大可汗之位的宣稱者展開。
如果說彌射、步真這些入唐突厥人對室點密形象的改寫,是對突厥官方歷史敘事的第一次關鍵性重構的話,那麼宋祁探索出的突厥早期世系便是對室點密形象的第二次重構。這兩次重構在沙畹及之後絕大多數學者那裡獲得了“歷史真實性”,從而產生了室點密形象的第三次重構——室點密、Ištämi Qaγan和Silzibul的融合。
在6世紀末的突厥人心中,包括室點密在內的最初兩位可汗取得擊敗柔然的重大勝利。到8世紀中葉,由於年代久遠,兩位可汗的功績被擴大為突厥建國和對外征服的全部事業。兩個官方記憶的演化邏輯相對清晰,說明突厥人對於室點密的認識是比較穩定的。6世紀末或7世紀初出生、7世紀30年代成為西突厥葉護的彌射和步真,對室點密的認識應當不會偏離官方敘事太遠。然而,《彌射傳》構建的先隸屬於大可汗,然後征服西域自為可汗並世統其眾的室點密,無論是與突厥汗國官方敘事,還是與突厥早期歷史相比,都有巨大沖突。親身經歷西突厥汗位由木杆系轉移至達頭系的彌射和步真,必然清楚“世統其眾”的大可汗家族是不存在的。《彌射傳》和《懷道墓誌》中的室點密形象顯然是彌射、步真家族對官方記憶的重構,目的在於建構自身合法性,這也迎合了唐朝經營西突厥故土的政治需要。
與第一次重構不同的是,室點密形象的第二次重構完全是《新唐書·西突厥傳》修撰者宋祁糅合不同來源、不同性質的材料,並融入自己對突厥分裂認識的產物。隋人是突厥分裂的見證者,他們對這一過程的記載最為可靠,明確指出是阿波可汗與沙缽略可汗的紛爭導致了分裂。對後世史家來說,突厥的分裂已是遙遠的過去,他們對此的認識越來越混亂。8世紀末修成的《通典》和10世紀修成的《舊唐書》,居然都把突厥的分裂歸結到不同時代的木杆可汗和沙缽略可汗的關係上去。11世紀的宋祁沒有意識到周隋時代史料的重要性,把不同時代、不同性質的關於突厥西部和西突厥汗國初期的記載等同視之,使得他不僅得出西突厥歷史至少應追溯至達頭可汗的看法,還構建了一份突厥早期世系。
宋祁的重構提醒我們,正史文本的正當性並非不證自明,而應成為嚴格甄別與仔細研判的對象,我們有必要揭示出那些孤立的、碎片的史料是如何被史家從原本的文本環境中抽離出來,整合成全新的歷史敘述的。室點密形象的第三次重構,就是由於現代史家未能將後世突厥人的歷史記憶、後世史家的重構與同時代的史料記載相分離,才被製造出來的。在北方民族史研究中,還有一些亟待解構的歷史敘述,例如過去以元修《遼史》為基礎構建起的遼史框架,在許多層面已經受到嚴峻挑戰。更進一步,這樣的重構當然不會是周邊民族史研究的特例,想必在史料更為豐富、積澱更為深厚的其他史學領域中也有類似情況,其中暗藏的史料、概念和方法上的問題有待學者重新審視。
(作者孟楷卓,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於子軒,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歷史研究》在線投稿系統已於2021年9月15日啟用,網址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點擊下方“閱讀原文”,關注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官方微店,訂閱《歷史研究》《歷史評論》和《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