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18日,病床上的建築師呂彥直依舊在等待南京中山陵竣工的消息。
不曾想,在其嘔心瀝血設計的工程即將完工之際,他便撒手人寰,年僅35歲。
此前一年,呂彥直被確診為肝癌,連續幾年的高強度工作很快耗盡了他的生命。
他曾說:“紀念性建築,一定要由中國人自己設計。”
由呂彥直一手設計的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都是極富中華民族特色的中國現代建築,以“西式為裡,中式為表”,用先進的西方建築技術和材料,表現中國古代建築的式樣。
遠看是中式建築,近看卻是西式結構,這就是中山陵和中山紀念堂最大的特色之一。
南京中山陵仿造古代陵寢而建,但其全部建築,包括牌坊、墓門、墓室、臺階等,全部是用鋼筋混凝土澆築而成。
廣州中山紀念堂的整個八角形屋身也是用鋼筋混凝土澆築成型,又在其框架加上琉璃瓦、大理石、廊柱、斗拱、藻井、雀替等仿古構件,融匯西方建築技術與東方建築藝術。
師夷長技而不忘本,在短暫的一生中,呂彥直為中國近現代建築事業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然而,他的名字卻曾消失長達四十年,他的成就也一度無人知曉。
呂彥直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讀經史。他的父親呂增祥是李鴻章和袁世凱手下親信,曾擔任駐日使館參贊,又與翻譯家嚴復結為親家。他在天津英租界附近有一座西洋式豪宅,袁世凱等新派官員經常在他家聚會一起嗨。
這一場人生變故,對呂彥直而言是不幸,對中國建築界而言,卻是幸運。孤苦無依的呂彥直在次年被二姐呂靜宜和二姐夫嚴伯玉帶到了法國巴黎,並在那裡讀了四年書。
嚴伯玉是嚴復之子,當時擔任清廷的駐法參贊。此人曾就讀於劍橋大學,頗有傳統士大夫的氣節,從不借職務之便為自己謀利,家裡窮得揭不開鍋,晚年更是在抗戰期間窮困而死。
小呂少年老成,也不想給姐夫增加負擔,於是每天放學後就去巴黎歌劇院外的停車場給人擦車,賺錢貼補學雜費。
1904年的第一場雪,比1903年來得更早一些,巴黎的冬季堪比東北那旮旯,別人寧願在家吹暖氣也不肯出門,呂彥直卻冒著寒風冷雨出外打工。那一年,他只有10歲。

在巴黎的四年裡,呂彥直親身感受到了西方教育的先進水平。隨姐姐、姐夫回國前夕,他的心中就埋下一顆種子,我一定會回來的。
回國後,呂彥直勤奮刻苦,成了“別人家的孩子”,考上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留美預備部。之後被公派留學美國,在康奈爾大學攻讀建築學。
翻開中國近現代史,康奈爾大學的中國情結尤為濃厚。這裡走出了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教育家任鴻雋、橋樑專家茅以升等知名華人校友,而呂彥直也將從這裡出發,成為中國建築界的頂尖人才。
學霸呂彥直讓嚴復的二女兒嚴璆為之傾慕,成了他的“小迷妹”。 嚴璆寫信給嚴復,請求父親也讓她去北京求學,之後赴意大利留學。
難得兩個年輕人志趣相投,呂、嚴兩家親上加親,為呂彥直和嚴璆牽線搭橋,正式定親。
本是一段美滿姻緣,卻成為他們各自人生的一大憾事。
1921年,在康奈爾大學畢業,並在美國工作兩年的呂彥直取道歐洲,打算回國創業。
在塞納河畔憑欄遠眺,年輕的呂彥直滿懷一腔熱血,他的夢想是設計和建造中國的“盧浮宮”、中國的“埃菲爾鐵塔”,讓全世界的人到中國參觀,讓各國遊客為之驚歎。
在盧浮宮,呂彥直偶遇英國利茲大學畢業的中國留學生黃檀甫。
黃檀甫來自廣東臺山縣一個貧窮山村,自小在英國利物浦做華工,所幸被一家英國人收養,因此得以接受正規教育。
黃檀甫在利茲大學毛紡系就讀期間,整個年級就只有兩個東亞人。和呂彥直一樣,他深刻認識到中國的落後,也希望能為祖國幹一番事業。
只是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兩名年輕學子從巴黎和會聊到五四運動,相談甚歡,結下了終生友誼。

一百年前的中國,海歸學子在國內的境遇並不輕鬆。
早在美國墨菲建築事務所上班時,呂彥直就曾參與設計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學校舍。回國之後,呂彥直第一站也是前往墨菲事務所的上海分所,繼續未完成的工作。
可是,公司的老油條處處刁難小呂,對他百般挑剔,工作氛圍令呂彥直不快。在洋人眼裡,建築事務所是他們的生意,中國人就只配搬磚。
山不轉水轉,幾個月後,呂彥直提出辭職。他很憤怒,明明是在中國,憑什麼要洋人說了算?
他堅信,自己有朝一日也能開辦建築事務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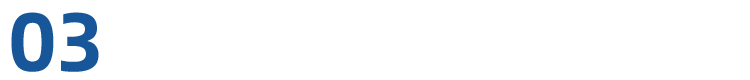
辭職之後,呂彥直在十里洋場的茫茫人海中漂泊。天下之大,竟沒有一處安身之地。彼時的上海,幾乎只有洋人的建築事務所,他們在中國大興土木,國人卻沒有發言權。
電影《中國合夥人》有一句臺詞:“掉進水裡你不會淹死,待在水裡你才會淹死。你只有遊,不停往前遊,那些一開始就選擇放棄的人他們不會失敗,因為他們從一開始就失敗了。”
呂彥直沒有放棄,在巴黎有過一面之緣的黃檀甫找到呂彥直,向他建議:“老呂,咱們一起合作,開創自己的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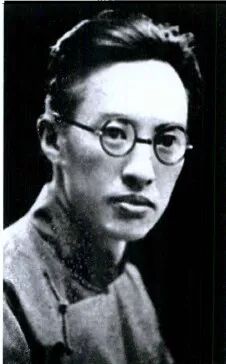
於是,兩個年輕人在上海合夥創辦了“真裕公司”,承接房屋設計和修繕業務,把中國人的建築事務所開到了洋人建築公司所在的辦公大樓裡,欲與洋人一爭高低。
真裕公司很小,這裡只有呂彥直和黃檀甫兩個人,黃檀甫負責對外聯絡業務,呂彥直負責建築工程,他們身兼數職,日夜忙碌。
真裕公司也很大,這裡裝的是中國第一代建築師的夢想。
真裕公司慘淡經營,幾年間一直默默無聞,直到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呂彥直終於得到了施展才華的機會。
當時,孫中山喪事籌備委員會公開向海內外徵求陵墓的設計圖案,並要求“圖案須採用中國古式而含有特殊與紀念之性質”。
這正是呂彥直多年來苦苦追求的,以西方先進技術建造中國特色建築。他果斷以真裕公司的名義參與這次競賽。
為此,呂彥直不顧戰火瀰漫下滬、寧的交通險阻,到南京東郊實地考察地形地貌,為畫圖打下堅實的基礎。而他的競爭對手們卻只依靠喪事籌備處提供的照片進行設計。
四個月裡,呂彥直為設計殫精竭慮,茶飯不思。他不斷修改畫作,每畫完一稿,就用桐油灰捏造設計模型,然後對著模型修改畫作,修改完後再捏造設計模型,如此循環往復,不捨晝夜。
歷經數十個不眠之夜,直到截止日前夕,呂彥直才最終敲定方案,繪製出陵墓的9張設計圖和1張祭堂側視油畫,並撰寫了《陵墓建築圖案設計說明》。
在呂彥直的設計中,“公共建築,為吾民建設精神之主要表示,應當採取中國特有之建築式”。中山陵完全體現了呂彥直的建築思想。
在南京東郊的紫金山,中山陵依山而建,石牌坊、陵門、碑亭、廣場等建築物有序地排列在一條中軸線上,莊嚴肅穆。
但呂彥直是用西方鋼筋混凝土的建築技術,構件了這樣一個傳統的中國樣式。
作品交上去,呂彥直和黃檀甫在漫長的等待中煎熬,是成是敗,在此一舉。
9月,中山陵圖案評獎結果終於揭曉,呂彥直的設計獲得第一名,真裕公司一舉中標!這是中國人首次打破洋人壟斷國內大型建築設計的局面。
獲獎後的呂彥直以個人名義成立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彥記事務所,隸屬於真裕公司,並被受聘為中山陵園建築師。他終於兌現了自己的承諾,為中國建造新時代的大型紀念性建築。
在簽訂了中山陵建築師的合同後,呂彥直又開始趕製全部工程詳圖。整整兩個月閉門謝客,他既要擔任設計師、建築師,又是繪圖員、會計員、審計員,身兼數職、長期加班讓其身體嚴重透支,他卻絲毫不在意。
等到1926年中山陵招標施工,呂彥直因勞累過度病倒在了工地上,被送往上海治療。
他的搭檔黃檀甫急忙代替他前往南京監工。在奠基典禮上,病中的呂彥直借黃檀甫之口,當著各界人士的面發表講話,闡述自己的建築思想。
他們認為,自民國十五年來,日見鬥爭之事而無建設之象。國家應設法提倡教育本國人才,興立有價值之建築物,希望民國建設時之永久的紀念建築日興月盛。
就在呂彥直養病期間,廣州中山紀念堂的設計比賽開始了。呂彥直毅然抱病參賽,再度拿起尺筆,在低燒不退的情況下於紙上構思設計。
莊嚴宏偉的廣州中山紀念堂,坐落於越秀山南麓。紀念堂四面為重簷歇山抱廈,拱托中央八角攢尖式巨頂,遠看是一座中國式的寶塔,內部雄偉空曠,可作為大型集會場所。中山紀念堂是廣州的標誌性建築,也是呂彥直短暫一生的又一力作。
但是,無論是中山陵還是中山紀念堂,呂彥直都沒能見到其修建成時的壯觀景象。
自知命不久矣,呂彥直寫信告知遠在北京的未婚妻嚴璆,讓她另作打算。
嚴璆卻痴心一片,在得知呂彥直不治後,斷然前往北京西郊出家,削髮為尼,從此長伴青燈古佛。

一直到去世前,呂彥直還在堅持工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首都建設出謀劃策,臥病在床期間起草了《規劃首都都市區圖案大綱草案》。
呂彥直始終沒有放棄“西式為裡,中式為表”的建築主張。
他希望南京結合美國華盛頓和法國巴黎的特點。在不影響交通和美觀的情況下,將城市分為三大部分,在舊城的基礎上營建新城,採取中國特有的建築樣式,保留明清遺址和部分城垣,且總體規劃設計,應由中國人擔任。
最終,呂彥直帶著未盡的理想,於35歲時英年早逝,他所主張的首都建設也沒能實現。
與其同時期的建築學家,如梁思成、劉敦楨等也有類似於 “西式為裡,中式為表”的主張。抗戰期間由他們組建的營造學社在戰火中,走遍祖國萬里河山,對各省的古建築進行考察和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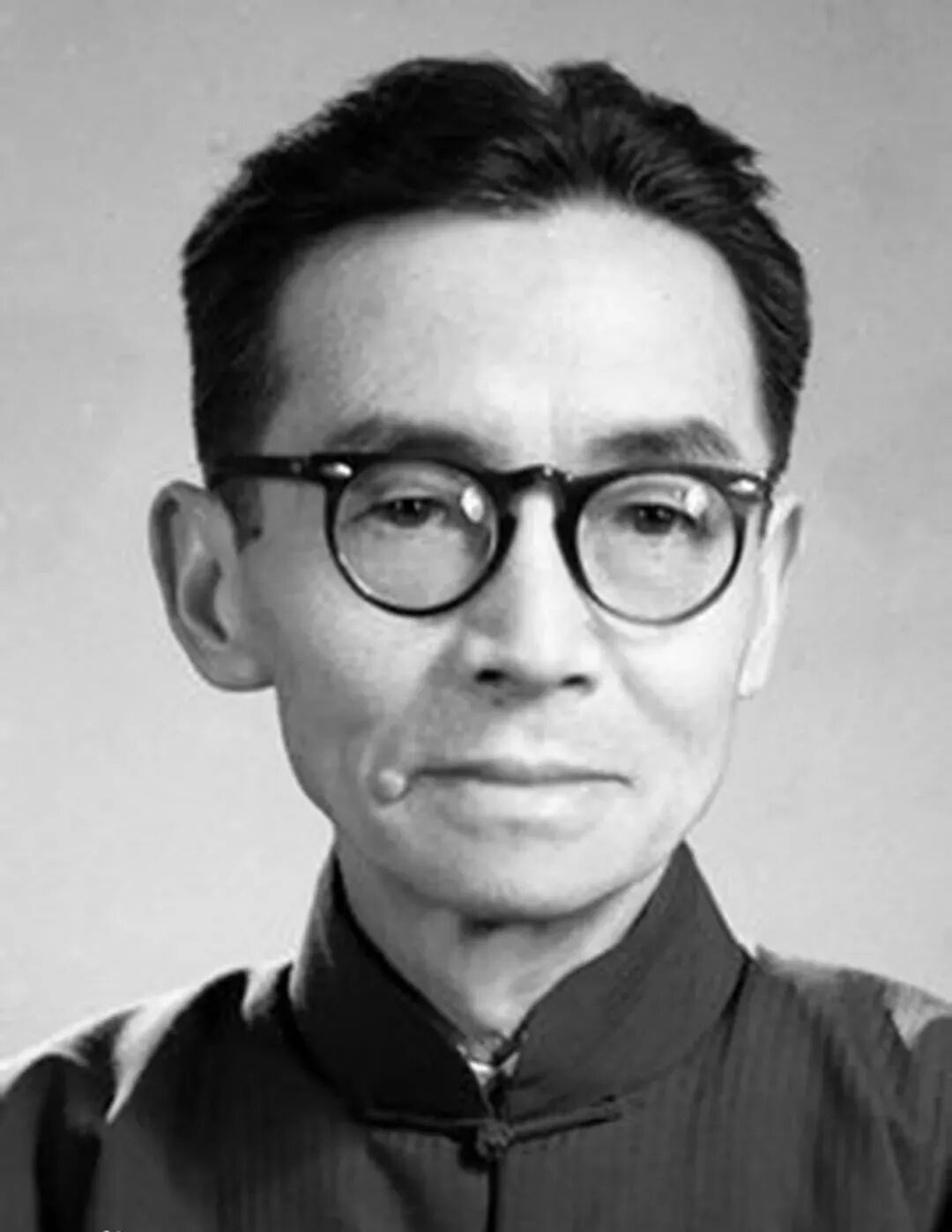
梁思成曾評價呂彥直:“到1920年前後,隨著革命的潮流,開始有了民族意識的表現……(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是由崇尚歐化的風氣中回到民族形式的表現,實為近代國人設計式樣應用於新建築之嚆矢,適足於象徵我民族復興之始也。”
可即便是梁思成,也在保護中國式建築的歷程中屢受波折。
呂彥直去世後,他的摯友黃檀甫請捷克雕刻家高琦為其雕刻一尊半身浮雕像,雕像下方還有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手書的一段碑文。讓呂彥直魂歸其一手設計的中山陵,是對其最好的紀念,也是寄託著黃檀甫深深的哀思。
這塊紀念碑原本鑲嵌在中山陵西南角,據以往的說法是毀於日寇佔領南京期間。
但據當代廣東研究會理事盧潔峰考證,呂彥直的紀念碑被毀於1956年。當時,中山陵曾遭到蘇聯專家的強烈批評。
後來,黃檀甫慘遭抄家。一夜,天降暴雨,黃檀甫家被掃蕩一空,大量衣物、書籍被查封。
半夜,黃檀甫的子女們還躲在房中,有些後怕。年逾古稀的黃檀甫卻拄著柺杖,藉著昏暗的燈光在一片狼藉的房間中翻找,嘴裡喊著:“圖紙啊,圖紙啊……”
原來,被踐踏的物品中,有他珍藏多年的呂彥直設計圖紙,那是其最珍貴的遺產,也是兩人友誼的見證。當看到這些圖紙毀於一旦,黃檀甫老淚縱橫,不禁失聲痛哭。
從那一天起,黃檀甫就像變了一個人,常喃喃自語道,不知道將來有何面目去見老友。
1969年,黃檀甫鬱鬱而終。據說,黃檀甫下葬之時,子女在他的口袋裡放了一張呂彥直的遺照,及其英國養母的照片。
此後,由於某些原因,很少有人再提呂彥直的名字,這位建築大師就這樣在歷史上“憑空消失”。
直到1998年,南京第二歷史博物館才將呂彥直的照片公之於眾,刊登在當年的《羊城晚報》上,呂彥直終於重回大眾視野。
此時,中國的建築行業也在改革的春風中崛起,但似乎與呂彥直的構想大相徑庭。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順手點贊、點在看讓我知道您在看~
盧潔峰:《呂彥直與黃檀甫:廣州中山紀念堂秘聞》,花城出版社,2007年版
賴德霖:《閱讀呂彥直》,《讀書》,2004年第8期
鄭曉笛:《呂彥直:南京中山陵與廣州中山紀念堂》,《建築史論文集》,2001年
金煥玲、周虹:《我國第一代建築師的職業價值觀及其當代啟示》,《華中建築》,2015年第10期
張開森:《呂彥直:用生命鑄就中山陵》,《中國檔案》,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