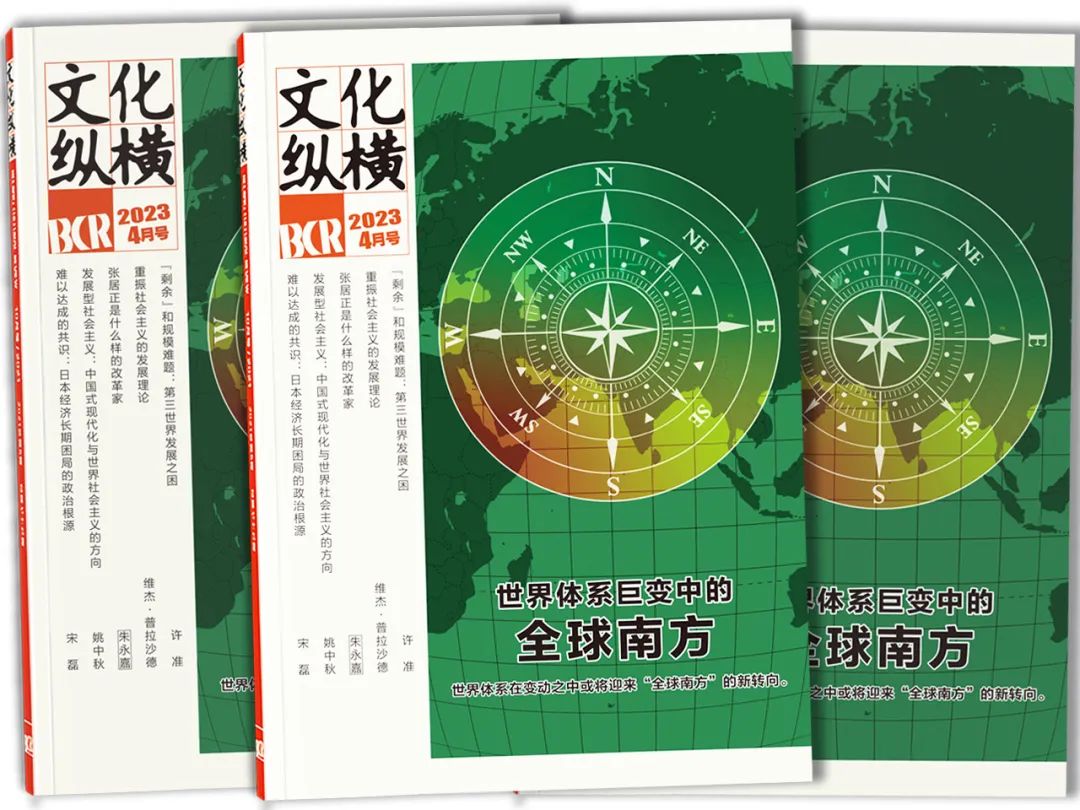
✪ 沈偉偉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導讀】據媒體報道,近期,韓國三星的半導體部門引入ChatGPT不到20天,就出現三起洩密事件;之後,意大利成為全球第一個禁用ChatGPT的國家;而ChatGPT則開始大規模封閉亞洲賬號……眼下,人工智能浪潮正衝擊世界,但技術的膨脹及其對人類行為的潛在支配,也引發恐懼和擔憂,牽出一個爭議已久的問題:互聯網,還可能自由嗎?或者說,當真有互聯網自由嗎?
本文從2023年初拜登簽署的《互聯網未來宣言》出發,重新審視“互聯網自由”及其背後的真相。作者指出,“互聯網自由”口號由來已久,它發端於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在2010年時任國務卿希拉里的“互聯網自由”主題演講中達至頂峰。然而,後來成立的美國“網絡自由工作組”以信息自由為名,藉助民主和人權話語,把“互聯網自由”變成一種足以影響他國政權穩定的話語輸出手段。從美國內部的“9·11”後大規模國內監控、阿蘭·斯沃茨自殺悲劇,到外部的推動阿拉伯之春、對他國發動網絡攻擊等,這些舉動最終毀掉了所謂互聯網自由的公信力。不僅如此,原本一體兩面的市場自由和信息自由,也出現難以彌合的裂痕。在擴張甚至壟斷的過程中,網絡平臺為自身利益而實施種種言論控制,甚至連官方都望塵莫及。如今,各國都致力於建立可控、可管的互聯網秩序,“互聯網自由”這一口號已成空殼。
作者認為,能不能在新國際格局下,打好和應對好“互聯網自由”這張老牌,成為中美兩個互聯網大國共同的考驗。拜登借《宣言》重提“互聯網自由”,與其對外尤其對華戰略有關;對中國而言,互聯網本身是機遇大於挑戰,關鍵在於爭取國際互聯網治理的更大話語權,並針對《宣言》和相關政策提出穩健而睿智的交鋒之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美國還能打“互聯網自由”這張牌嗎?》,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人工智能(AI)作為科技前沿的熱門話題,其發展一直為人矚目;而在大國競爭中,誰能更好地開發和利用AI,就將在未來佔得先機。1月27日,美國和歐盟首次在該領域達成合作協議,雙方將在預測極端天氣和應對氣候變化、應急響應、醫保事業、電網運行,以及農業發展等五大重點領域就AI的應用展開合作。協議中的一段話耐人尋味:
“今天的聲明也建立在《互聯網未來宣言》中提出的願景之上,即在全世界建立一個開放、自由、可靠和安全的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我們期待著通過這一倡議深化我們與歐盟的合作。”
《宣言》系去年年中由美國總統拜登牽頭簽署,該宣言一共兩頁半,沒有什麼深文奧義,僅羅列了幾大價值,可重點還是重申“互聯網自由”這一老套口號。雖說如此,《宣言》背後所蘊含的戰略佈局,無疑值得我們結合科技治理的內外新形勢,來重新思考應對之策。
▍命運多舛的《互聯網未來宣言》
其實,這份由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彼得·哈勒爾和白宮技術政策特別助理、哥大法學院教授吳修銘牽頭制定的《宣言》謀劃已久,但無奈廟堂朝野阻力頗大。一方面,由於早期媒體披露的草案要求籤署國只能使用“值得信賴的”網絡設備,外界視其為夾帶私貨打擊中國製造,沒有主義,只有生意。更讓互聯網自由分子憂心忡忡的是,這類聯盟目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另起爐灶將稀釋掉其他聯盟的努力,特朗普的“清潔網絡計劃”就是前車之鑑。
然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最終比原計劃晚了半年多,拜登領銜大筆一揮,《宣言》湊齊了61個國家。可仔細考察簽署國名單,全球網民數前十的國家中,竟有四國缺席——前兩名中國和印度、第五名巴西、第八名俄羅斯。中俄本是《宣言》鬥爭對象,沒上榜天經地義。印度和巴西也由於此前國內互聯網管制,被排除在外。可是,就算是這61個國家,又有哪個國家未曾違背《宣言》宗旨呢?哥倫比亞軍方剛被聲討針對記者和政客的監控,尼日爾才經歷十天之久的全境封網,匈牙利和以色列還在為間諜軟件Pegasus挑起的事端背鍋。就連美國“自己人”英國,前腳剛簽署《宣言》,後腳就在議院繼續推動強化內容管制的《在線安全法案》。這些都大大削弱了《宣言》的影響力,也因此《宣言》不大可能對互聯網國際治理格局帶來實質性影響。總的來說,拜登政府的這步棋,並不是什麼高瞻遠矚,充其量只是以“互聯網未來”之名,為“互聯網自由”招魂。
▍什麼是“互聯網自由”?
“互聯網自由”口號由來已久,發端於克林頓政府第二任期,興盛至特朗普上臺前。其間,“互聯網自由”發展出兩層內涵:市場自由和信息自由。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
首先,互聯網自由中的市場自由,是新自由主義在互聯網產業的體現。美國通信產業的擴張始於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當時,美國經濟內外交困,內陷經濟滯脹,外臨日歐大敵;於是,以里根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開出去管制(de-regulation)藥方,一步步顛覆了從進步運動、新政時代以來的經濟政策。互聯網產業興起後,無論是民主黨當政,還是共和黨上臺,延續此前去管制政策基調,給孵化期的互聯網企業開了多盞綠燈,由此成就硅谷繁榮。[1]
關於互聯網自由的討論最初聚焦的是市場自由,可是市場自由固然重要,但其影響侷限在經濟領域,對國際政治、國際社會的影響有限。很快,美國便發掘出互聯網自由的另一副面孔——信息自由,它將帶來更持續的國際影響力。一開始,克林頓政府並不強調信息自由。基於當時對互聯網的理解,信息自由不言自明,無須爭取。的確,互聯網技術剛出現時,幾乎所有專家都認為,互聯網技術將徹底顛覆傳統主權國家對輿論的管控。經典表述出自克林頓政府首席技術政策專家邁格辛納:
“互聯網技術短期內使主權國家對信息的控制變得更加困難,並且長遠看來,信息終將擺脫主權國家的干預”。
政府控制互聯網信息,就如同“把果凍釘上牆”一樣困難。
不曾想,沒過幾年,“果凍”真就上了“牆”:各國政府不但利用掌握的技術搞信息審查,甚至可以指揮更懂技術的互聯網平臺搞信息審查。這麼一來,反而把信息自由這一層面的“互聯網自由”意識形態威力給襯托出來:信息自由的本質,一言以蔽之,恰恰是反對國家干預信息的自由傳播,這一點與美國冷戰以來的外交姿態一拍即合。因此,小布什政府除了繼承和推進克林頓政府市場自由這份政治遺產之外,也在信息自由層面做足了文章。為此,小布什還專門成立“全球互聯網自由工作組”(GIFT)督辦此事,其使命就如其英文簡稱,到處送禮撒錢,資助各類促進互聯網自由的公民組織和技術項目。
接下來數年間,白宮的類似論調不絕於耳,其高光時刻無疑是2010年1月21日,時任國務卿的希拉里發表題為“互聯網自由”演講。希拉里一方面談理念,強調互聯網自由之於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談現實,她巧妙地將互聯網自由與國家安全聯繫起來,主張當前互聯網自由現狀已“威脅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利益”。[2]在“互聯網自由”這面大旗下,倘若一國政府過度審查和干預互聯網內容,就會被扣上互聯網不自由、侵犯人權的帽子。通過將互聯網自由對接上民主和人權話語體系,希拉里為美國政府直接干預他國政治做了強力背書。
就在這一通洋溢著振奮之情的演講一個半月後,奧巴馬政府以GIFT為班底,改頭換面成立新的“網絡自由工作組”,落實互聯網自由事業,其資金支持比小布什政府更大,也更具針對性——超過1億美元被用於資助加密、反內容審查技術工具和相關民間組織。正是在希拉里演講後,互聯網自由開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嶄露鋒芒。表面上,它關心的是信息的自由與否,但實際上,隨著互聯網的全球化與平民化,它逐漸成為一種足以影響他國政權穩定的話語輸出。並且,美國經過多年經營,已手握兩大保障:其一,互聯網自由的直接受益者是微軟、谷歌、臉書、推特等美國互聯網平臺,它們具備技術和市場的全球統治地位,藉助這種統治地位,也為了延續這種統治地位,它們不遺餘力地將互聯網自由的邏輯和話語,推廣到其國際商業版圖的每一寸領地。其二,互聯網領域頗有影響力的自治組織,長期以來多由美國政府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互聯網域名管理就是其中典型,直到2016年,美國政府才極不情願地移交控制權。
美國在互聯網基礎設施控制權上的絕對優勢,讓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當然,它們也沒有坐以待斃,在信息控制、隱私保護、數據安全等方面與美國推行的互聯網自由開闢戰場,致使這些美國互聯網巨頭和自治組織也無法置身事外,輕則被罰沒,重則被拉黑。即便在外略有阻力,“互聯網自由”在希拉里演講之後一時間成了國際外交的關鍵詞之一。儘管很難把當年年底興起的“阿拉伯之春”完全歸功於希拉里演講,但後續史料披露也表明,這次在蘇東劇變之後全球最大的區域政治格局變動,也與美國有直接關聯。[3]互聯網自由給美國帝國主義開了一扇便門,不戰而屈人之兵。

▍“互聯網自由”消亡史
“互聯網自由”看起來形勢一片大好,成為動員群眾星火燎原的社交網絡熱詞。然而在隨後幾年內,這一理念卻屢遭挫敗,跌下神壇。可以說,本世紀最初二十年,前十年是火山爆發,頂峰是希拉里演講;後十年是熔岩冷卻,冷水是一盆接一盆。
第一盆冷水,便是美國在互聯網自由問題上的屢次心口不一、自相矛盾。比如,在希拉里演講後不久,維基解密爆料,希拉里親自向美國外交官下令網絡監聽他國外交情報,甚至還監控聯合國秘書長。一國情報機關的這類監控,在外交領域本算不上什麼新鮮事,但希拉里高調演講在先,再出手就是打臉。這類自相矛盾並不止這一起。內有“9·11”後大規模國內監控、阿蘭·斯沃茨自殺悲劇,外有推動阿拉伯之春、網絡攻擊伊朗核設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當然,互聯網自由戰略的最大挫折,還是來自斯諾登事件,該事件披露了美國國家安全局對全球電話和互聯網進行監控的情況,各大美國互聯網公司都參與其中,監控對象不僅包括其戰略敵手,也包括本國公民和西方盟友。可以說,斯諾登徹底打破了美國政府原有的互聯網自由戰略路線圖。直到奧巴馬政府後期,奄奄一息的互聯網自由理念,已不再具備希拉里演講時的號召力。正如哈佛法學院古德史密斯教授所言,美國從未毫無保留地堅守互聯網自由,也不是兩手乾淨到未曾插手控制本國和他國互聯網,因此美國大可不必,也沒資格以“互聯網自由”王國自居。[4]
歷史有時很弔詭。新自由主義浪潮雖然給互聯網自由的第一副面孔市場自由注入源動力,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催生的右翼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浪潮,把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後者中斷了美國一貫的互聯網自由立場,不再強調國際自由市場和基本人權這套普世價值,甚至在某些領域徹底甩掉偶像包袱,築起貿易壁壘,直呼“美國優先”。在特朗普任期內,媒體真假新聞之辯、“黑命貴”運動中的言論封控、國會山後特朗普被推特和臉書封號等事件,加速了互聯網自由的消亡。這些事件單看可能無關宏旨,但串聯起來,毀掉了美式互聯網自由的公信力。
第二個挫敗來自互聯網自由內涵自身的演變:原本一體兩面的市場自由和信息自由,出現了難以彌合的裂痕。互聯網自由的兩個層面通常被認為不可分割:市場自由是信息自由的保障,而信息自由反過來又會促進市場自由。互聯網“端對端”架構,流淌著自由基因,越自由越發展,越自閉越萎靡,這似乎已成鐵律。難怪希拉里演講時信誓旦旦,“那些限制信息自由或者侵犯網民基本權利的國家,將自絕於新千年(互聯網產業)發展機遇之外”。然而,近年曆史表明,二者關係並不是雙向奔赴這般簡單。
首先,市場自由並不必然促進信息自由。市場自由意味著去管制,二者互為表裡。可現實是,隨著平臺的擴張甚至壟斷,平臺對互聯網的控制程度越來越高,其為自身利益而利用技術設下種種言論控制,手法之隱蔽,範圍之精準,政府有時也望塵莫及。因此,脫離管制的平臺可能成為信息自由的新敵人,馬斯克接手推特後的一系列鬧劇就是例證。信息控制也未必導致市場萎靡,中國就是典型。中國不但孵化出世界第二大互聯網產業,而且在數字支付、電子商務、新一代網絡設施、人工智能等領域大有趕超美國之勢。這就讓帶著傲慢與偏見的“互聯網自由”擁躉們難以理解。
其次,即便在信息自由的制度建設方面,對比2010年希拉里演講時,美國也不斷“開歷史倒車”。必須承認,美國作為“互聯網自由”倡議者,在信息自由方面,向來是全球表率。其最重要的制度保障是1996年《傳播風化法》第230條款。該條款規定,除知識產權等極少數領域,對於網民在平臺上發佈的信息,平臺無須承擔任何責任。230條款背後是憲法第一修正案,230條款是面子,第一修正案是裡子,這種信息自由,全球獨此一家。
然而,面對越發強勢的互聯網平臺及其背後超越主權國家的全球資本,美國政府也開始擔心:信息太過自由,會不會遭遇反噬?例如,正是由於法律責任的豁免,違法成本下降,使得美國社交平臺成為謠言、假新聞、仇恨言論、恐怖主義的“歡樂谷”。於是,近些年風向轉變,美國也開始限制信息自由,強化內容治理,其中最成功的改革是2017年限制網絡賣淫信息自由流通的《禁止網絡性交易法案》。僅在2021~2022年間,美國參眾兩院就醞釀了20多個法案,都致力於改革230條款,它們大致分四類:完全推翻230條款;限制230條款適用範圍;增加網絡平臺義務;限制網絡平臺主動審查用戶言論。可以預見,230條款未來即便不被完全推翻,也必將進一步受限,而在它庇護之下的信息自由理念也將隨之受挫。
或許因為互聯網自由自身的無力,近些年,美國互聯網自由戰略在國際上也面臨重重阻力。以其戰略伙伴歐盟為例,就不是一味順從美國,通過《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和《數字服務法案》等立法舉措,限制美式互聯網自由理念。就像歐洲老闆德夫納寫給美國老闆施密特的那封公開信說的,
“從我們歐洲人自身角度出發,我們害怕谷歌,因為它威脅到我們的價值,威脅到我們的人性,威脅到全球社會秩序,以及歐洲的未來”。
而且,不管美國願不願意,互聯網自由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地讓步於互聯網秩序。各國政府正在拆分互聯網,鑄造物理的或虛擬的數據和信息壁壘,目的是在民族國家內部劃出一片更可控的網絡空間。在數字時代,國內數據和信息的控制,成為各國內部治理的關鍵;而能不能最大程度地把握數據和信息的國際流動,構建一個對本國有利的國際互聯網秩序,成為其對外政策的組成部分。無論是拆分,還是控制,這都與早期互聯網自由的願景背道而馳。無怪乎從希拉里演講後,民間機構統計全球互聯網自由度一路下跌,這表明一個大趨勢:儘管程度不一、手法各異,但各國政府都在不斷將曾經開放自由的互聯網,分割成一塊塊越發可控的自留地。或許在美國人眼裡,這些自留地下面就埋葬了其苦心經營的互聯網自由理念。
“現如今,美國和中國在互聯網自由議題上有分歧,我們坦率而一致地解決這些分歧。畢竟,這不僅是關乎互聯網自由,而且關乎我們未來整個世界。”
十三年後,回味這句話,讓人不禁感慨:隨著互聯網秩序不斷遭遇挑戰,中美在互聯網自由這個議題上的分歧在縮小,反而是雙方“積極、合作和密切關係”隨著新冷戰的升溫,迎來比以往更大的考驗。能不能在新國際格局下,打好和應對好“互聯網自由”這張老牌,成為兩個互聯網大國共同需要面對的考驗。
拜登此番借《宣言》為“互聯網自由”招魂,並在後續科技治理政策中一再強調,自然是與其對外(尤其對華)戰略部署有關。平心而論,儘管消亡徵兆不斷湧現、矛盾之處暴露無遺,但其所傳達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野心未必完全沒有市場。這是因為其背後依然有一整套多年積累下來的、以自由民主為核心的話語體系支持,它對於絕大多數美國普通民眾甚至西方普通民眾仍有一定吸引力。況且,哪怕“互聯網自由”就此消亡,還可能出現其他新提法。對於技術人員和網絡用戶規模都位居世界第一的中國而言,互聯網本身永遠是機遇大於挑戰,我們能否審時度勢,爭取在國際互聯網治理中更大的話語權,並針對《宣言》和相關政策提出穩健而又睿智的交鋒之策,尚有待進一步觀察。
註釋:
[1] Jeff Kosseff, The Twenty-Six Words That Created the Interne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Anupam Chander,“How Law Made Silicon Valley,”Emory Law Journal, Vol.69, 2014, pp. 639.
[2]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Archived Content, January 21, 2010.
[3] Evgeny Morozov, 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Public Affairs, 2011.
[4] Jack Goldsmith,“The Failure of Internet Freedom,”in David E. Pozen ed., The Perilous Public Squa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4月刊,原題為《美國還能打“互聯網自由”這張牌嗎?》,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