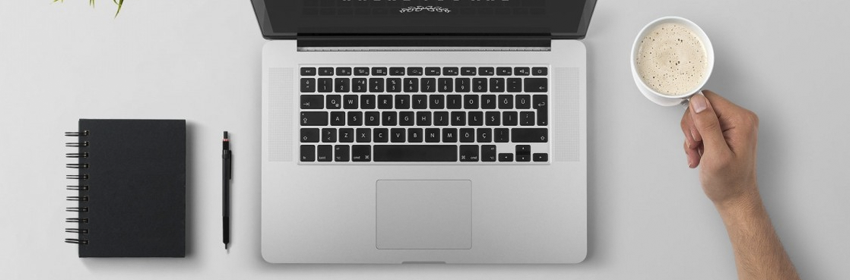|作者:餘馳疆
|排版:徐一冉
《長空之王》是一部特殊的影片。首先是題材特殊,聚焦試飛員這個並不為人所熟知的職業:人民空軍成立70年來,試飛員們成功試飛了180餘種、超過2萬架飛機,是國產飛機從無到有的幕後英雄。
其次是拍攝特殊,不論是中國飛行試驗研究院(簡稱試飛院)、試飛烈士陵園等場地,還是殲-16、殲-20等戰機,以及那些堪稱“魔鬼式”的日常訓練,許多內容都是第一次出現在大銀幕上。
· 《長空之王》海報。
作為片中大隊長張挺的飾演者,胡軍早在24年前就在電影《沖天飛豹》中演過試飛員。“上世紀90年代我們去西安閻良(試飛院所在地)時,那還是很荒涼的一個地方;如今不光是武器裝備,包括整個機場的建築、設施,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對記者說。
不止設備,新一代試飛員也已經成為科技型人才。如同電影裡王一博飾演的雷宇,他們懂技術、懂外文,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是真正把藍圖送上藍天的人”。
“唯一沒有變的就是激情,這幫人太有激情了!”
最後再拉三下拉環
《長空之王》的故事主要圍繞兩代試飛員展開:雷宇展現的是新一代試飛員成長、成熟的淬鍊,張挺則是體現了中生代的職責與擔當。電影中,除了講述兩代人的飛行故事,還有不少筆墨聚焦他們的家庭和生活——飛行外的硬漢張挺,就是一個對妻兒溫柔備至,對家庭有所愧疚的普通男人。
因此,電影也將驚心動魄的試飛戲、大場面戲和質樸無華的生活戲穿插推進,藉此還原真實的試飛員故事。“我們拍攝的時候,導演身邊永遠都有一兩位技術專家或者試飛員,每一個專業鏡頭都要問一句:這個動作合理嗎?”胡軍說,“我也是試飛員手把手教出來的,操控杆怎麼操作,檢查飛機時按鈕、掰手在什麼位置,蹬舵的時候一定要回頭看……”
長時間訓練,一方面是為了不在表演中出現硬傷,但更重要的是對職業、對人物產生本能的認知。拍攝中,那封催人淚下的遺書被胡軍改了不下20遍,“有一天晚上睡不著,乾脆起來再寫一遍”。
每一次落筆,胡軍都對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意。影片籌備期間,劇組專程去試飛員公墓祭拜。拍攝時,張挺對著同僚的墓碑傾訴,拍出來不到一分鐘,其實胡軍在那裡坐了很久,既講劇本上的臺詞,也說著自己的心裡話,“聊到最後眼淚不停地掉下來”。
70年中,32名試飛員為祖國獻出了生命,平均年齡40歲,最年輕的僅僅22歲。張挺的謝幕戲,就是在試飛新機型時不幸犧牲。拍這場戲,胡軍坐進模擬機艙,在裡面停留了很久。“我在想那時的情緒該是什麼樣的?人的反應究竟是什麼?他不會想我要當英雄,誰都不想犧牲,誰都想活下去。”胡軍說,“怎麼表現呢?你不能光哭光嚷嚷,首先他是一名軍人,其次他是一名專業的試飛員。”
胡軍和導演提出,最後再拉三下拉環(用於戰鬥機緊急彈射),那是人本能的求生反應。“那個瞬間,張挺是很不甘心的,他會想我就這麼走了嗎?好多事情我還沒做,沒陪爸媽去趟北京,沒陪兒子踢一場足球,沒跟媳婦補拍婚紗照,沒看到最新機型成功呢!”
最後,張挺面對死亡,抬頭看著天,對著對講機說:“我已無法返航,你們繼續前進。爸媽、老婆、兒子,我愛你們。”
這條拍完,導演說:“就是它了。”
不是為了情懷而拍情懷
張挺犧牲的戲,是全片情緒最濃的情節,也是觀眾最受觸動的部分。首映禮時,一位老軍人站起來對胡軍說:“我真是服了你了,怎麼淚點全讓你攥在手裡了。”
《長津湖》的雷公、《長空之王》的張挺,硬漢胡軍成了兩部戲中最催淚的存在。在他看來,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英雄角色不僅有“神性”,更具有人性。如同張挺的拉環,雷公的犧牲也並非“直給”的催淚。《長津湖》前半部分,原定雷公的形象非常冷酷,胡軍則通過設計一些小細節把人物熱愛生活的一面表現出來,比如掛在耳朵上的簡易擴音器、用子彈殼做成的煙桿等。
原劇本中,雷公在臨死前對連長和指導員說:“要帶好七連,爭取把每個人都帶回家……”臺詞很多很滿,胡軍和導演商量,最後壓縮成了兩句。一句是“疼死我了”,一句是“別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他把口號式的謝幕,轉化為充滿個人情感的下意識表達。“他只是想回家,落葉歸根,不想留在異國他鄉。”
恰恰是這些迴歸人性的呈現,讓兩個傳統式的英雄角色引起了觀眾更深的共鳴。“以前我們看所謂的主旋律,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是符合年代需求的。但如今,觀眾需要回歸真實感,而不是舉著胳膊喊口號的主旋律。”胡軍說,“沒有必要說主旋律就必須是‘主旋律’,非要把這個主題單拎出來,而是應該通過演員演繹、電影表現,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大家自然會感受到你想表達的情感。”
演過許多英雄人物之後,胡軍對這種類型的角色有了自我要求:“不是為了情懷而拍情懷。”
《長空之王》路演第一站就是閻良的試飛院。胡軍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放映場面:一個大機庫裡,兩架殲-11停在兩邊,打著藍色的光,中間是一個巨大的銀幕,2000多人一起觀看。坐在胡軍旁邊的是一位試飛員,他全程沒有出聲,默默落淚。觀影結束,他用力攥了攥胡軍的手,然後轉身離開。
一切感動,盡在不言中。
速度太快,想認真都認真不起了
喬峰、項羽、趙雲、雷公、張挺……胡軍擔得起“英雄專業戶”的名號。2018年,他參演李六乙導演的話劇《哈姆雷特》,很多人都懷疑:“硬漢怎麼演憂鬱王子呢?”李六乙說:“胡軍一站上臺,大家就知道這是個英雄。但當英雄把自己的憂鬱和彷徨展現出來,戲劇張力會非常大。”
· 胡軍在電視劇《天龍八部》中飾演喬峰。
某種程度上,這種反差就是胡軍能將一個英雄角色詮釋得深入人心的原因:他總在尋找英雄身上一些反英雄的特質。就像在喬峰身上,他不僅看到武俠世界的俠肝義膽,也看到了喬峰與阿朱兒女情長裡的堅決、單純和執著。“有人味兒,是真男人。”
人味兒,是他在採訪中經常提到的詞。講到兒時看過的電影,《烏鴉與麻雀》《龍鬚溝》《聶耳》《青春之歌》;講到自己崇拜的演員,石揮、趙丹、於是之;講到父親、大伯作為歌唱家的創作經歷,在海上與水兵同吃同住,在蒙古包沉浸地體驗生活……
“因為他們經歷過那個年代,生活在那個年代,演出的真實感是我們無法替代的。一個演員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氛圍裡浸泡了很長時間之後,出來的東西才可信。”他話鋒一轉,“可是,現在速度太快了,不論是電影和電視劇,都太快了。”胡軍懷念讀書時、剛入行時那種排練、讀劇本,一點點摳、一點點打磨的時光,但現在“想認真都認真不起了”。
“只能保有自己的堅持,私底下多去琢磨,不能因為外界的速度就對自己放低要求。”胡軍對自己的要求,就是儘可能塑造一些更有創造性的角色,比如去年殺青的劇集《黑土無言》。在這部東北題材的懸疑劇裡,胡軍飾演了一個完全不英雄的底層小人物。
“演員們分兩種,一種演自己的自然狀態,就是可以把控的狀態;還有一種就是創造性的,去塑造一個完全跟你不相關的人物——這個角色就是這樣的。”
胡軍認為演員最重要的就是發現自己的可能性,他把這個職業比作一塊膠泥,既通過思考和身體塑造角色,也通過角色和舞臺塑造自己。
“這就是表演給我最大的愉悅。”胡軍說。
關注人民文娛
點一下你會更好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