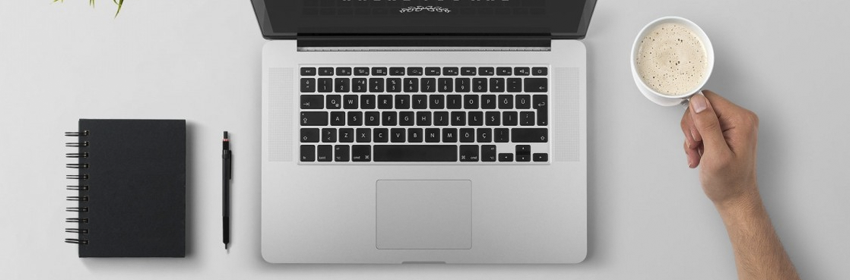|作者:許曉迪
|排版:徐一冉
2021年深秋,話劇《驚夢》首演定在國家大劇院,後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
票都退了,面對空無一人的劇場,劇組完成了第一次演出。演完,導演陳佩斯心裡坦坦蕩蕩、乾乾淨淨,沒有一絲波瀾。“但我篤定了,”他說,“篤定這個作品就立在這兒了,從此什麼都不用擔心。”
故事說的是解放戰爭背景下,一個崑曲班子的生死存亡。60年的老昆班“和春社”,於戰火紛飛中困在兵戈相接的平州,看家好戲《牡丹亭》演不成,轉而披掛上陣,將一出夾生的《白毛女》搬上舞臺;又陰差陽錯,把“赤色宣傳”唱進了國軍兵營。
“既應承了您的戲,無論如何也得唱完。”這是劇中班主童孝璋(陳佩斯飾)的臺詞。兩年來,《驚夢》巡演到了第三輪,其間種種輾轉遭際,取消、延期、停演,“十幾口人云遊在外,各種車船店腳牙,很苦”。編劇毓鉞回憶,學著劇中夥計念起臺詞:“班主,咱這一站一站的,說話間可就走不下去了。”
5月1日,《驚夢》走到了第五十場演出。在豆瓣評分系統中,中國話劇的前三甲是《茶館》(9.4分)、《驚夢》(9.3分)、《戲臺》(9.2分)。《茶館》無需多言,北京人藝的經典,從於是之到濮存昕,演過了一甲子;《驚夢》與《戲臺》,是近十年的兩出新戲,都出自陳佩斯與毓鉞的合作,一個導演、主演,一個編劇。
兩部戲,講的都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亂世,都是一個戲班的掙扎求存,都是喜劇的外殼裹著悲情的底色。“梨園小天地,天地大梨園。我們都是戲班裡的人,我們都在舞臺上,隨時粉墨登場,不斷變換角色。”毓鉞說。
熱心腸、冷筆墨
幾十年前,毓鉞就想寫一部關於舞臺的戲,“它的意涵很寬泛,人生、社會,都是個舞臺,前面後面,兩副不同的樣子。有些人,從前邊看很光鮮,從後邊看很齷齪;也有些人,前面看著很虛偽,後面看著很真實。”他寫了個開頭,下文卻一直沒著落。
2014年,陳佩斯找到毓鉞,想琢磨一出新戲。
兩人相識於上世紀70年代。毓鉞所在的總政話劇團排《萬水千山》,演員不夠,從八一廠拉來了陳佩斯湊數。倆人一個演匪兵甲,一個演匪兵乙,同時兼著效果組的活兒,舞臺上需要打雷下雨了,就在後面鼓搗出“嘩嘩譁”“咔咔咔”的動靜。
此後30多年,風雲流散,各謀生路,陳佩斯演小品、弄喜劇,毓鉞當編輯、寫劇本。倆人再碰頭,毓鉞把塵封的幾頁稿紙翻了出來。
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在瞎聊天,天上一腳地下一腳。等真趴桌子上寫,兩個月,毓鉞就遞來本子。陳佩斯看了,哈哈大笑,又覺得像小刀片剜心頭肉似的疼。
2015年7月,《戲臺》正式開演,陳佩斯說,人生60年,就是為了等這部戲。
劇中,他演京劇班主侯喜亭,面對軍閥威權,步步妥協退讓,裡外不是人。洪大帥愛聽老鄉的嗓兒,他讓包子鋪的夥計翻身成角兒,演上楚霸王;洪大帥要求霸王穿紅袍,他拿出《法門寺》裡劉瑾的戲服,讓英雄披上太監的行頭;洪大帥不讓霸王別姬,他咬牙改戲,項羽東渡烏江,從頭收拾舊山河……
“下輩子我要再吃這碗開口飯,我是您孫子。”“不就是胡說八道嗎?咱們來。”“這叫什麼東西!我這不是跟著造孽嘛!”小人物的苟且與不甘,藉著嬉笑怒罵的臺詞,傾灑而出。
《戲臺》裡,從小百姓到大人物,各有難言的悲楚。陳佩斯說起做案頭的時候,常常陷入情緒,想找個地方蹲著哭。毓鉞也有這種感覺,但拿起筆來,傷心就已放下。“有作者說,寫作時熱淚盈眶,打溼了稿紙,我說,最後你肯定把這段刪掉。寫作不是情緒奔放,要以冷峻的態度處理心中波瀾,一句話咀嚼又咀嚼,冷靜地控制每一個字,用最好的橋段;要冷冷地詢問自己:你在幹什麼?你在說什麼?你敢不敢剖開自己放在人性堆兒裡碾壓一番?你還有沒有對這個世界說話的熱情和勇氣?”
《戲臺》問世後,票房口碑雙雙飄紅,毓鉞和陳佩斯打算接著來,做成“戲臺三部曲”,“完成一次人生舞臺的歷練”,《驚夢》就此續上。
故事的背景仍是戰亂年代,毓鉞原還想寫京劇班,最後一幕唱“紅淨”關公,半人半神、氣魄非凡。他約了陳佩斯,跑去雲南,在民宿裡聊著聊著,覺出了不對勁。“關公美是美,但他是戰爭的化身。東漢末年,殺人如芥,過五關斬六將、水淹七軍、火燒赤壁,多麼慘烈,我們要用這個形象結束這出戏嗎?”最後,他們選擇了崑曲,一個更為純美、脆弱的藝術化身。
· 毓鉞(左)與陳佩斯在雲南麗江聊劇本。
劇中的和春社,不懂政治、不諳國事,只想守著祖宗傳統唱戲掙錢,卻被捲入時代的漩渦。當硝煙散盡,夢驚已是新天地,童孝璋站在漫天大雪中高聲獨白:“與各位看官因戲結緣,無關在天在地,在陰在陽,應了的戲就得唱,這是祖師爺定下的規矩,和春社伺候大戲《牡丹亭》,與看官同樂。”古戲臺緩緩推出,杜麗娘、柳夢梅一襲淡粉嫩綠,唱起《驚夢》一折,戰爭中逝去的亡魂,一一走過臺前。
“《驚夢》的第一主題是和平主義,用羅曼·羅蘭的話講,人類要超乎混戰之上。這很難做到,我們嚮往天下大同,卻生活在一種不能自已、無法掌控的悖論中。戲的結尾,鬼魂們在花神的引領下上臺,藝術之美向所有人敞開,無論生死、貴賤。”毓鉞說,“一個文藝家一生的使命,就是去接近本質、接近善良,用端正的心靈感悟世界,而不是傾瀉醜惡、煽動仇恨,為了某種短淺的目標,甚至一己私慾,扯破嗓子吆喝,那是一種卑劣。”
長肉的日子
盛產文藝家,是毓鉞他們家族的特色之一。
他原名愛新覺羅·恆越,恭親王奕訢的後裔,生長於北京東單的小院中,與那座被譽為“半部清朝史”的王府已無太多關係,但昔年的餘裕閒散,仍散落在生活裡。他曾在採訪中回憶兒時,拿著珊瑚頂子當彈球玩,摔碎了兩尺高的官窯花瓶,大人也不著急,叨咕一句“挺好看,怪可惜了的”。
10歲那年,趕上“文革”,學校裡沒有一塊完整的窗戶玻璃,毓鉞天天在外晃悠。後來,他從家裡翻出一把破京胡,聽著收音機裡的樣板戲,學會了全出。
為了“穿上那件綠衣服”,他到處報考文工團,被總政話劇團看中,招進小樂隊。那一年,他14歲,除了拉胡琴,演出時也當個群演,扮扮某甲某乙。
總政有個小圖書館,二三萬冊書,打著封條,釘上了木板。他偷偷鑽進去,怕被抓住,摸出一本就跑,摸到什麼看什麼,不明白也看,“只要是字”。同事之間也互相借,一大厚本,通宵地讀,不睡覺,如此六七年,度過了荒瘠的青春。
轉業後,毓鉞進了當時熱門的糧油外貿總公司,“剛去就往家扛糧食,發棗,把我媽高興壞了”。這種生活沒留住他,他找了個機會,調去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劇本》月刊,去過“真正長肉”的日子。
那是1984年,改革之風勁吹,文藝界春潮湧動,陳凱歌、張藝謀拍了《黃土地》,崔健組了“七合板”樂隊,阿城寫了《棋王》。這一年,陳佩斯初登春晚,對著一個空碗吃麵條,笑翻了全國人民。
毓鉞被分到月刊的戲曲組,結交了不少戲曲作者:以一曲《新亭淚》牽動舉國情的鄭懷興,在《曹操與楊修》裡寫透“兩個刺蝟的擁抱”的陳亞先,創作出《評劇皇后》的地道“老廣”郭啟宏,還有在湖南衡陽寫祁劇的劉和平——此時離《大明王朝1566》誕生,還有20多年。
毓鉞和劉和平都對清史感興趣,見面即聊興大起。毓鉞寫過一篇小文,講劉和平少年時的捕蛇軼事:一次,他被眼鏡王蛇咬住手指,送去醫院已周身紫漲,救回來一條命,卻留下了一根殘指。不久前,兩人在一次會上碰見,劉和平至今沒“陽”,說是被毒蛇咬過,百毒不侵,新冠也沒轍。“還吹牛呢”,毓鉞笑道,當年種下的友誼延續至今,“七老八十了,見著面還嗷嗷亂叫”。
那時,《劇本》編輯部在東四八條52號,兩間屋子,擠擠挨挨的。“但那是個文化堡壘。”毓鉞說,“我們樓上是《人民文學》,獨領風騷的大刊,和那些老編輯們天天吃飯亂串。旁邊是《美術》,有畫展就被拉去,在美術館前面找一個地方,抽菸、喝啤酒、聊藝術。對門還有《音樂》和《詩刊》。天天在這些人中間,想起來都美。”
他隔空沉浸在那段時光裡,整個人亢奮起來。
“大家樓上樓下地跑,戰友一樣。到處都是開不完的會,只要談文學、談藝術,就是一家人,你插不上嘴,就自然淘汰。當然,也可以坐旁邊聽著,人也不轟你。”
“劇協的領導,張穎、劉厚生,要水平有水平,要胸懷有胸懷,年輕人誇誇其談,他們樂呵呵地聽著。”
“戲劇界也是漂亮的時候,天天出作品,目不暇接,直接介入時代、介入生活,現象級的紅火。作為編輯,每天都在興奮中,從自然來稿中發現一個好苗子,幫他們改,能發表、能演出,比作者還高興。”
“生活挺艱苦的,自己帶著盒飯,發了稿費,能在小飯館要倆菜,好牛。沒人惦記吃什麼、穿什麼,每天像海綿一樣,瘋狂地成長,看作品、聊戲劇,喝著窮酒,通宵達旦,不知疲倦……”
“我甚至覺得,我一直在消化當年那點營養。”當回憶結束,他說,“那是長肉的東西,不能放棄,絕對不能放棄。”
人類的最後一幕是喜劇
那段火熱美好的年月,燃燒了六七年。進入90年代,“文化堡壘”漸漸解體,“大家各自找生計,走的走、散的散”。
毓鉞開始做電視劇編劇。“那時電視劇比較熱乎,組多,從業人員也多,但混好了也不容易,淘汰率極高。”他寫的第一部長篇電視劇是《李衛當官》,首播於2001年,徐崢、陳好、唐國強主演。
· 電視劇《李衛當官》海報。
對毓鉞來說,有了對戲的研究,駕馭電視劇並不難。《李衛當官》是古裝喜劇,戲說的外殼下有正劇的底色。一個目不識丁、油嘴滑舌的底層平民,陰差陽錯當了官,以其無知和無畏,讓貪墨成風的官場顯出原形,又在盤根錯節的權力博弈中,保持著草根的反骨。
《李衛當官》大火後,毓鉞沒有接著寫續集,“狗尾續貂沒意思”。幾年後,他寫了一部《李衛辭官》。他更喜歡這個“有點厚度”的故事。雍正死了,李衛老了,年輕的乾隆登基。老臣李衛看透了官場與皇權,一心想辭官歸裡,可越想躲越躲不過;少君乾隆心高氣盛,面對這個“老油條”,既不喜歡又要重用,氣也不能、恨也不能。
· 電視劇《李衛辭官》海報。
在這個“老臣戲少君”的故事裡,毓鉞有自己的寄寓。少年時代,他從總政圖書館摸出的第一本書是翦伯讚的《中國史綱》,從那時起便定下志向,此生要無情地揶揄帝制,對自己的祖宗做一堅決反叛。
“明朝末年,社會已經敗象盡生,中國本應與世界同步,在腐朽中開始新生。是我們這些吃生肉、騎光屁股馬的‘野蠻人’,拉家帶口二三十萬人入關來,完成了一次本不應該的迴光返照,中國封建帝制突然像一顆流星,再次劃過天空,又延續了280年。”他說,“不能因為我的姓氏,失去了對歷史的另一種權衡和考量。”
潛入歷史與人性的深處,這是毓鉞寫戲的宗旨。“戲劇不是用來分辨對錯的,是用來體味、體驗的,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前幾天,他看了一個紀錄片,一群小蝌蚪,歷經千難萬險,回到大海的懷抱,感動得直掉眼淚,“那裡面有人生的況味”。
回望走過的路,毓鉞覺得其中的扭結和反差,是一種悲劇感,也是喜劇感。他的微信頭像是“憨豆先生”羅溫·艾金森,一個牛津的高材生,扮演著無聊幼稚、戲謔孤獨的倒黴蛋。毓鉞喜歡這種英式的幽默,以自嘲面對冷冷的人生。
毓鉞所懷念的80年代的文化盛景,底色是宏大與深沉,喜劇則是邊緣的、低人一等的藝術。世事流轉,當一切塵埃落定,他有了另一番感悟。“過去我看什麼都很悲,現在看什麼都很樂,都像喜劇。‘人類的最後一幕是喜劇。’這是馬克思說的。”
喜劇要讓人笑,可是笑亦有道。“拿葷段子咯吱人,不講結構純粹靠口彩,那不叫喜劇,那叫段子。喜劇是一種對人生的歸納總結,是一種個人意識的表現,它是一種精神,是一種靈魂,是一種看世界的態度和方法。喜劇可不是逗樂,喜劇跟滑稽是兩碼事。”毓鉞說。
笑,是一種帶鹽分的泡沫。這是哲學家伯格森的比喻。笑跟泡沫一樣,閃閃發光。它是歡樂,但把它掬起來嚐嚐味道的人,會從裡面發現苦澀。
“進廟燒香,入山門第一盈殿,必是那個笑呵呵的大肚彌勒。世上苦難多多,你笑什麼呢?隨閱歷漸增,我慢慢覺得他那笑是有道理的,世間萬相,苦集寂滅,若換個位置看,比如坐在他的那個位置看,沒準兒真的是很可笑的。”在《戲臺》的創作談中,毓鉞寫道,“真正的喜劇,好的喜劇,其底蘊絕不可笑。正如彌勒之笑,他笑的背後,是深深的悲憫。”
關注人民文娛
點一下你會更好看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