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仁貴
來源:《歷史研究》2022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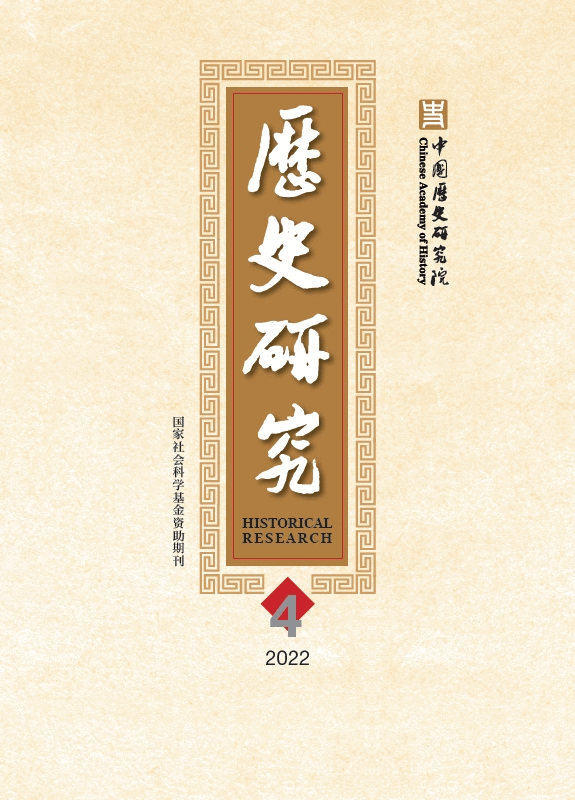
摘 要: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作家認為海洋環繞的“人居世界”可分為三部分,將之命名為歐羅巴、亞細亞和利比亞,古羅馬人繼承了此劃分方式並把利比亞改稱阿非利加。中世紀前期,基督教吸收並融合了古希臘羅馬的“陸地三分說”和挪亞三個兒子(閃、含、雅弗)劃分世界的猶太典故,歐亞非三大洲的洲際話語由此牢固確立。從本質上看,“陸地三分說”是歐洲中心主義對已知世界的認知和想象,它把文明與野蠻、自由與專制的對立以及等級觀念,投射到世界不同區域及其民族身上,構成所謂“歐洲優越論”的邏輯起點。
關鍵詞:陸地三分說 人居世界 歐洲中心主義 洲際想象 歐洲優越論
在陸地表面區域劃分問題上,洲是沿用至今最重要的地理單位之一,它作為不可置疑的“地理常識”幾乎被人們廣泛接受。從源頭上看,所謂“歐洲”、“亞洲”、“非洲”概念及其劃分,來自古希臘羅馬人把已知世界分為三部分的觀念,即“陸地三分說”(Tripartite Division of the Earth)。在希臘化時代,它被猶太思想家拿來與挪亞三個兒子劃分世界的聖經典故對應,而後經基督教吸收融合,到中世紀前期被確立為主導歐洲的世界認知範式。近代以來,以歐亞非為代表的洲際話語,被歐洲以外的地區廣泛接受,成為各自區域的身份認同,也是地緣政治和文明範圍的奠基性概念,產生了深遠影響。
“陸地三分說”既是一種地理分類和空間區分,有助於界定和識別世界不同區域,也是一種文化想象與認同構建,蘊含著自我與“他者”、空間與等級、話語與權力等政治內涵。雖然人們廣泛使用歐亞非洲際話語,但學界對該話語的產生、接受史以及思想內涵研究不夠。本文擬從古典作家對“人居世界”的劃分入手,考察公元前6世紀至15世紀末歐洲關於“陸地三分說”的歷史演變,揭示背後蘊含的身份認同、權力關係和世界認知。
早期文明伊始,人類就開始探索自身居住大地的形狀、構造及劃分,逐漸發展出被稱為“地理學”的學問。在希臘語中,“人居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oikoumene)是關於人類所居住世界形狀和範圍的概念,源自希臘語動詞“οἰκέω”(意為“居住”)。實際上,該詞是古希臘人對已知人類居住世界的總稱,因此也被理解為“已知世界”(known world)或“熟知世界”(familiar world)。由於材料匱乏,我們無法全面掌握“οἰκουμένη”一詞在早期希臘的使用情況。該詞主要被用來區分有人居住的世界和無人居住的世界,它的首次使用可能是在公元前8世紀至前6世紀大殖民時代希臘人與更大範圍的人群遭遇之時。通過在地中海範圍內長距離旅行和探索,古希臘人對地中海以及周邊世界有了明確認知,其知識精英對已知世界及其形狀進行勾勒,推動了“οἰκουμένη”概念的使用。
儘管《荷馬史詩》沒有提及“οἰκουμένη”一詞,但該書為後來古典作家探討“人居世界”的形狀奠定了基礎。在討論阿喀琉斯之盾(Shield
of Achilles)的章節中,《荷馬史詩》描繪了“鍛造之神”赫菲斯托斯打造圓形世界之盾,整個大地被描繪為狀若盾牌的平坦圓盤,其外圍被一條大洋河環繞。公元前6世紀早期,著名數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地圓說”(Spherical Earth),即“人居世界”是一個巨大的球面。
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人對“人居世界”的劃分取得重要突破,這得益於以米利都為中心的愛奧尼亞學派(Ionian school)的貢獻。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約前610—前546年)和赫卡泰烏斯(Hecataeus,約前550—前476年)等認為不存在單一世界大陸,“人居世界”被水道分為若干部分,這些部分被稱為“洲”(ἤπειρος),意為被寬闊水道分隔的大片陸地。把“人居世界”劃分為幾部分的做法,很大程度上來自古希臘人的航海經驗,古希臘水手進入愛琴海準備靠岸時,常把左舷方向稱為歐羅巴,右舷方向稱為亞細亞。但古希臘人在“人居世界”的劃分問題上還存在以下幾大分歧。
其一,陸地究竟應該分為兩部分還是三部分。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利比亞應該被視為亞洲的一部分還是單獨的一部分。古希臘地理學家赫卡泰烏斯強調,“人居世界”由兩部分構成,歐羅巴在北部,亞細亞(包括利比亞)在南方;但阿那克西曼德認為利比亞是第三部分。公元前5世紀,“人居世界”分為三部分的觀念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希羅多德雖然對該觀念表示疑問,但在《歷史》敘述中仍沿用歐羅巴、亞細亞和利比亞三部分的表述。利比亞作為“人居世界”第三部分的直接有力證據是,公元前474年希臘詩人品達創作《皮提亞頌歌》,把利比亞與歐羅巴、亞細亞並列,稱為第三大洲。
其二,幾大洲的邊界問題。幾乎所有古典作家都認為,水道是洲際之間的分界線,但具體在哪裡並不確定,僅有地中海作為歐洲和非洲之間的邊界沒有爭議。關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邊界,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烏斯認為是高加索的菲西斯河(Phasis);隨著希臘化時代地理知識的發展,這一邊界被修訂為塔奈斯河(Tanais,即後來的頓河)。關於亞洲和非洲之間的邊界,人們通常認為是尼羅河。但希羅多德認為,把尼羅河作為利比亞與亞細亞的邊界並不合適,因為尼羅河東岸也屬於埃及;少數古羅馬作家把蘇伊士地峽作為亞洲和非洲的邊界,不過主流觀點仍然認為兩者的邊界是尼羅河。
其三,幾大洲各自的面積和長度問題。古典作家對幾大洲的面積作了估計,據說繪製首張世界地圖的阿那克西曼德認為,歐羅巴、亞細亞和利比亞的面積差不多,而赫卡泰烏斯主張“人居世界”兩大部分的歐羅巴和亞細亞(包括利比亞)面積一樣大。就幾大洲的長度而言,希羅多德認為歐羅巴的長度是其他兩大洲的總和,他寫道:“人們把世界劃分為利比亞、亞細亞和歐羅巴三部分,在我看來這是令人驚訝的,因為三大洲之間相差太大。歐羅巴的長度相當於其他兩大洲之和;歐羅巴的寬度,在我看來,也是亞細亞和利比亞加起來都無法比擬的。”
儘管古典作家對“人居世界”的劃分存在上述分歧,但也有基本共識。例如,他們都認為陸地外圍環繞著海洋,類似於一個“世界島”,內部被水道分為若干部分。這條環繞陸地的海洋被稱為“大洋河”(Okeanos/River Ocean),其名稱來自古希臘神話中的泰坦巨人俄刻阿諾斯(Oceanus),分隔幾塊大陸的水道都通向大洋河。此外,古典作家普遍把地理方位與氣候條件聯繫起來。古希臘人根據氣候條件把大地分為溫帶、寒帶、熱帶等氣候帶;除溫帶以外,其他地區因極度寒冷或炎熱,被視為不適宜居住之地。
到希臘化時代,由於與外部接觸範圍不斷擴大,特別是亞歷山大東征後,“人居世界”的範圍得到拓展。波里比阿寫道:“由於亞歷山大在亞洲建立的帝國和羅馬人在世界其他地區建立的帝國,幾乎所有的地區都變得可接觸了……我們能夠獲得更好的知識,尤其是關於從前鮮為人知的土地真相。”“人居世界”的地理知識在希臘化時代極大增長,人們把歐洲與亞洲的邊界從菲西斯河改為塔奈斯河,這種界定隨後被古羅馬地理學家繼承。
與古希臘人一樣,古羅馬人對描繪“人居世界”也很感興趣。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64—公元23年)系統總結了從荷馬到埃拉托色尼的地理知識,認為“人居世界”是被海洋環繞的“斗篷狀”(chlamys-shaped)巨大島嶼。老普林尼寫道:“整個環狀大地分為三大部分:歐洲、亞洲和非洲。世界起點在西部的直布羅陀海峽,大西洋在那裡衝入並延伸到內海。從海洋進入時,右邊是非洲,左邊是歐洲,中間是亞洲;它們的邊界分別是頓河和尼羅河。”
古羅馬人通過持續軍事征服,將地中海周邊地區納入統治之下,其世界觀很大程度上受古希臘人影響,但也進行了一定的改造和發揮。在拉丁語中,“人居世界”的詞彙是“orbis terrarum”(意為“環狀大地”),即羅馬統治下的已知世界。古羅馬錢幣和圖像中刻有權杖、地球、花環和船舵的圖案,以及勝利女神(Victoria)腳踩在地球上的形象,象徵著羅馬征服整個陸地和海洋。普魯塔克注意到,龐培“在三次勝利中征服了整個世界”,首先征服利比亞,其次征服歐羅巴,最後征服亞細亞。狄奧尼修斯對羅馬的統治地位如此讚歎道:“羅馬人的城市統治著整個陸地……她統治著所有海洋,不僅是赫拉克勒斯石柱以內的海洋,還有所有可以航行的外圍大洋;她是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權力範圍同時橫跨日出之地和日落之地的城市。”為了加強帝國統治,古羅馬人設置了許多行省,例如把原屬迦太基的地區改稱阿非利加行省,愛琴海以東設置小亞細亞行省(Asia Minor)、大亞細亞行省(Asia Major)等,體現了羅馬帝國的洲際色彩。
公元前5世紀,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在談及“人居世界”三部分的名稱時說:“我無法想象為何會有三個名字(亞細亞、歐羅巴和利比亞),尤其它們都是女性的名字,被賦予一塊實際上是一個整體的陸地;我認為,也不應該把埃及尼羅河和菲西斯河作為邊界線;我說不清是誰給這三塊土地起的名字,或是他們從哪裡取的綽號。”由此可見,在希羅多德時代,人們並不清楚三大洲名稱由來,它們之間的分界線也不甚明確。
“歐洲”(Europe)一詞的拉丁語為“Europa”,來自希臘語“Εὐρώπη”,由“εὐρύς/eurús”(意為“寬闊、廣闊”)與“ὤψ/ōps”(意為“眼睛、臉、面容”)構成,意為“視線寬闊”或“範圍寬廣”。從詞源學上看,該詞主要存在“閃語說”和“印歐語說”等觀點。“閃語說”認為,“Εὐρώπη”與阿卡德語詞彙“erebu”、腓尼基語詞彙“ereb”同源,意為“日落”或“西方”。學者邁克爾·巴里在一塊亞述石柱上發現“ereb”一詞,意為“日落(之地)”,與意為“日出(之地)”的“asu”相對。“印歐語說”對該詞的閃語來源表示質疑,認為“Εὐρώπη”自線形文字B出現時就已在古希臘境內使用。此外,學者羅伯特·比克斯認為,該名稱源於印歐人到來之前,他在古馬其頓境內找到多處名叫“Eurōpos”的地方。“Εὐρώπη”與古希臘女神歐羅巴(Europa)同名。在古希臘神話中,歐羅巴是腓尼基國王的女兒,眾神之王宙斯化作一頭白色公牛誘拐了她,把她帶到克里特島,並生下兒子米諾斯(Minos)。“Εὐρώπη”一詞更可能來自東地中海地區,根據文化遷移理論,該詞與許多近東語言存在關聯,很可能由從事航海活動的腓尼基人傳入愛琴海地區。
目前已知最早從地理學上使用“Εὐρώπη”一詞的是大約寫於公元前6世紀的《荷馬頌詩·阿波羅頌》,其寫道:“特爾弗薩,我打算在這裡建造一座最美麗的神廟,給所有人以神諭,在這裡他們將永遠為我獻上完美的大祭。無論是生活在多岩石的伯羅奔尼撒人,還是生活在歐羅巴和被大海包圍的島嶼上的居民,在尋求神諭時都會進行獻祭。”歐羅巴在此被用來指稱希臘半島北部地區,與海島和伯羅奔尼撒地區相對。作為“人居世界”一部分的名稱,歐羅巴的稱呼被阿那克西曼德和赫卡泰烏斯使用,而後被希羅多德沿襲。
“亞洲”(Asia)一詞源自希臘語“Ἀσία”,在古代語言中,亞細亞與歐羅巴幾乎是含義相對的孿生詞彙,因此該詞的來源也具有“閃語說”和“印歐語說”不同觀點。“閃語說”認為,“Ἀσία”來自閃族語系的阿卡德語詞彙“asu”和腓尼基詞彙“asa”,意為“日出”、“東方”,引申為“日出之地”。持“印歐語說”的學者提出不同看法,認為“Ἀσία”早在線形文字B時期就存在於古希臘早期的人名和地名中,例如邁錫尼等地有個名為“Potnia Aswiya”的神祇;《伊利亞特》提及安納托利亞西部卡斯特河岸上有個地方名叫“亞細亞草地”(Ἀσίω λειμώνι/Asian meadow)。在古希臘神話中,忒提斯和俄刻阿諾斯有三千個女兒即大洋神女,分散在四面八方,侍奉大地和海洋,其中就包括歐羅巴和亞細亞。
作為一個洲際概念,“Ἀσία”來自古希臘人對外部“他者”的稱呼,並非亞洲人的自我稱謂。在希臘語中,安納托利亞(Ἀνατολή)意為“東方”、“日出”,該地通常被稱為“小亞細亞”。雖然荷馬和赫西俄德均提及“Ἀσία”一詞,但直到赫卡泰烏斯和希羅多德等時,該詞才被明確用於指稱“人居世界”的一部分,尤其是希羅多德用“Ἀσία”來稱呼安納托利亞和波斯帝國,以區別於古希臘人所在的愛琴海以西地區。從地理範圍看,“Ἀσία”的指稱範圍不斷東延,從呂底亞(前13世紀)到安納托利亞西部(前7世紀)、安納托利亞半島(前6世紀早期),再到安納托利亞及以東廣大地區(前6世紀晚期)。古羅馬人征服東方後建立小亞細亞和大亞細亞兩大行省,前者位於安納托利亞地區(今土耳其地區),後者位於地中海東岸(今伊拉克和敘利亞地區)。
作為“人居世界”的一部分,指代地中海南岸的大陸名稱經歷從“利比亞”(Λιβύη/Libya)到“阿非利加”(Ἀφρική/Africa)的轉變。“Λιβύη”源自一個名為“Libu”的柏柏爾土著部落,它在《奧德賽》中指埃及以西的肥沃地帶,公元前6世紀泛指地中海南岸地區。到公元前1世紀,斯特拉波仍在使用“利比亞”概念。公元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戰爭羅馬人攻佔迦太基後,在新徵服地區設立“阿非利加行省”(Africa Proconsularis),此後“阿非利加”逐漸取代“利比亞”成為“人居世界”第三部分的稱謂。
從詞源學看,“Ἀφρική”源自希臘語“Ἀφρικανός”(意為“不冷”),拉丁語為“Aprica”(意為“陽光充足的”)。有關非洲名稱的來源有許多不同理論,流行觀點認為,“Ἀφρική”來自埃及以西一個土著部落阿非利(Afri),其陰性形式為“Africus”,意為“阿非利人之地”,該詞後來泛指地中海以南的區域。另有學者認為,“Ἀφρική”來自腓尼基詞彙“ʿafar”(意為“塵土”),後者與拉丁語後綴“ica”(意為“土地”)組合起來的新詞即“塵土之地”(a land of dust)。該詞也可能源自柏柏爾語“ifri”(意為“洞穴”,引申為“穴居者”),被利比亞西北部的柏柏爾部落巴魯伊夫蘭(Banu Ifran)使用。
上述詞源學考察表明,歐羅巴和亞細亞很可能來自近東地區的閃語,通常與太陽所在的方位有關,分別對應西方(occidens,意為“日落之地”)和東方(oriens,意為“日出之地”)。公元前6世紀赫卡泰烏斯的《大地環遊記》(Periodos Gés)分為“論歐羅巴”和“論亞細亞”兩卷,對“人居世界”兩大部分分別給予地理描述,表明最晚在公元前6世紀就已存在歐羅巴和亞細亞的洲際概念。利比亞最初在亞細亞範圍內,公元前5世紀早期發展為獨立的洲際概念,從而構成“人居世界”的第三部分。隨著地理知識的不斷增長,洲際概念的範圍從愛琴海沿岸逐步向腹地擴展。歐羅巴從希臘擴展到泛希臘地區,到中世紀前期向西、向北擴展,逐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歐洲。亞細亞一開始指愛琴海東岸的安納托利亞西部,後來擴展至與古希臘人對立的波斯及其周圍地區,再後來泛指歐洲以東區域。利比亞/阿非利加起初僅指地中海南岸的小塊地區,後來擴展為對地中海以南、尼羅河以西區域的統稱。
起源於古希臘的“陸地三分說”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地中海區域其他文化元素,例如,羅馬人把“人居世界”第三部分的稱謂從利比亞改為阿非利加,希臘化時代猶太思想家把它與挪亞三個兒子劃分世界的猶太典故相對應。中世紀前期,在融合古希臘羅馬和猶太人關於世界劃分的觀念基礎上,基督教對歐亞非三大洲進行神學解釋,使之成為主宰中世紀歐洲的地理觀念。地圖史學者大衛·伍德瓦德分析道:“隨著古典傳統影響的減弱,《聖經》的來源變得更加突出。雖然最初是羅馬式的,但世界三分圖式的基本結構,應歸功於挪亞後裔在大地上居住的傳統。閃、含和雅弗的家族在地圖上經常被完整列出,他們的名稱來自《創世記》中的章節。”
作為早期基督教世界認知的主要來源之一,挪亞三個兒子劃分世界的觀念集中體現在《聖經·創世記》第10章“列邦列國”(The Table of Nations)的民族誌敘述中。其中說道,大洪水過後挪亞的三個兒子分散到世界各地,構成各地人群的起源:“出方舟挪亞的兒子就是閃、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親。這是挪亞的三個兒子,他們的後裔分散在全地。……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洪水以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該敘述還對挪亞三個兒子給予不同評判,閃和雅弗受到祝福,含及其後裔被詛咒要做其兄弟的奴僕。在希伯來語中,“Shem”(閃)意為“名字”,“Ham”(含)意為“炎熱”或“黑色”“Japheth”,(雅弗)意為“寬闊”或“擴展”。值得注意的是,“列邦列國”敘述只是籠統提及挪亞三個兒子及其後裔分散在各地,並未專門命名各自的領地。
亞歷山大東征開啟了希臘化時代,到公元前3世紀,一些猶太人逐漸接納古希臘的“人居世界”觀念。《聖經》七十士譯本對希臘語詞彙“οἰκουμένη”的使用達44次,主要出現在《詩篇》和《以賽亞書》中;七十士譯本把兩個希伯來語詞彙“ ”和“
”和“ ”均翻譯為“οἰκουμένη”,其中“
”均翻譯為“οἰκουμένη”,其中“ ”的翻譯使用更為頻繁,有33次。隨著猶太思想與希臘思想的交流碰撞,一些猶太文獻吸收通行於希臘世界的地理知識,例如大地的形狀以及劃分,並與猶太傳統的世界觀對接起來。根據公元前2世紀中葉猶太教文獻《禧年書》中的描寫,挪亞把大地分給三個兒子,閃得到“大地中間”的溫帶,其中錫安山“位於大地肚臍的中央”;含分得炎熱的南部地區,而雅弗分得寒冷的北部地區。很顯然,這種世界劃分觀念受到古希臘有關洲際劃分和氣候理論的影響,同時又把它納入《聖經·創世記》的解釋框架中。
生活於希臘化城市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思想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公元前20—公元50年)在其著作中使用了歐洲、亞洲和利比亞的概念,但沒有把它們與挪亞三個兒子的領地聯繫起來:“如果我家鄉的城市得到你們善待,那麼受益的就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人居世界各個地區的無數其他城市,無論它們是在歐洲、亞洲還是利比亞。”目前已知最早將希臘羅馬的歐亞非三大洲與挪亞三個兒子領地明確對應的做法,出現在猶太曆史學家約瑟夫斯(公元37—100年)的《猶太古史》中。約瑟夫斯指出,雅弗的後代分佈在歐洲、含的後代在非洲、閃的後代在亞洲:“挪亞的兒子雅弗有七個兒子,他們最初居住在塔努斯和阿曼努斯山一帶,後來從亞洲一直延伸到塔奈斯河,主要居住在歐洲”;“含的子孫控制著……阿曼努斯山脈和利巴努斯山脈一帶的國家……這個地區已經改名為利比亞,它得名於梅薩烏斯的一個兒子;我將說明它為什麼也被稱為阿非利加”;“挪亞的第三個兒子閃有五個兒子,他們住在亞洲,從幼發拉底河開始,直到印度洋”。
”的翻譯使用更為頻繁,有33次。隨著猶太思想與希臘思想的交流碰撞,一些猶太文獻吸收通行於希臘世界的地理知識,例如大地的形狀以及劃分,並與猶太傳統的世界觀對接起來。根據公元前2世紀中葉猶太教文獻《禧年書》中的描寫,挪亞把大地分給三個兒子,閃得到“大地中間”的溫帶,其中錫安山“位於大地肚臍的中央”;含分得炎熱的南部地區,而雅弗分得寒冷的北部地區。很顯然,這種世界劃分觀念受到古希臘有關洲際劃分和氣候理論的影響,同時又把它納入《聖經·創世記》的解釋框架中。
生活於希臘化城市亞歷山大里亞的猶太思想家斐洛(Philo of Alexandria,公元前20—公元50年)在其著作中使用了歐洲、亞洲和利比亞的概念,但沒有把它們與挪亞三個兒子的領地聯繫起來:“如果我家鄉的城市得到你們善待,那麼受益的就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人居世界各個地區的無數其他城市,無論它們是在歐洲、亞洲還是利比亞。”目前已知最早將希臘羅馬的歐亞非三大洲與挪亞三個兒子領地明確對應的做法,出現在猶太曆史學家約瑟夫斯(公元37—100年)的《猶太古史》中。約瑟夫斯指出,雅弗的後代分佈在歐洲、含的後代在非洲、閃的後代在亞洲:“挪亞的兒子雅弗有七個兒子,他們最初居住在塔努斯和阿曼努斯山一帶,後來從亞洲一直延伸到塔奈斯河,主要居住在歐洲”;“含的子孫控制著……阿曼努斯山脈和利巴努斯山脈一帶的國家……這個地區已經改名為利比亞,它得名於梅薩烏斯的一個兒子;我將說明它為什麼也被稱為阿非利加”;“挪亞的第三個兒子閃有五個兒子,他們住在亞洲,從幼發拉底河開始,直到印度洋”。
受《聖經》的影響,早期基督教思想家認為,人類世界的區分是在大洪水之後出現的,他們把挪亞三個兒子的領地與希臘羅馬的三大洲對應起來,頻頻借用閃、含、雅弗的典故來解釋三大洲的由來。4世紀教父、烏加大拉丁文版《聖經》譯者哲羅姆,從《聖經》中尋找世界劃分為三大洲的依據,“(大洪水過後)挪亞把世界分作三部分給三個兒子閃、含、雅弗為業,這三部分分別是亞洲、非洲和歐洲”。教父奧古斯丁描繪了三大洲的面積:“整個世界由亞洲、歐洲和非洲構成。這並不是平等的劃分。亞洲從南邊延伸到東邊和北邊,歐洲從北邊延伸到西邊,非洲從西邊延伸到南邊。歐洲和非洲合起來佔據世界的一半,亞洲單獨佔據另一半。”5世紀中葉里昂主教尤歇爾(St. Eucher)強調挪亞三個兒子的領地與歐亞非三大洲對應,“大洪水過後,挪亞的三個兒子佔據著世界的三個部分。閃的後代延伸到亞洲或東方,含的後代延伸到非洲或南方,雅弗的後代延伸到歐洲……或西方”。
到中世紀前期,歐亞非三大洲與挪亞三個兒子領地之間的對應關係牢固確立起來,這種對應關係還體現在當時的地圖繪製上。中世紀基督教發展出一種“世界地圖”(mappae mundi),成為時人理解天地和宇宙的重要方式。T-O地圖是中世紀歐洲有關“陸地三分說”的理想化表達,它把世界圖像濃縮成直觀具體的圖形公式,為中世紀基督教的世界認知確立基礎模型。T-O地圖起源於7世紀塞維利亞主教伊西多爾,其百科全書著作《詞源》(Etymologiae)成為中世紀基督教有關世界地理知識的基礎。《詞源》第14章《地球及其組成部分》寫道:“地球(orbis)由於是圓形而得名,因為它像一個輪子,這個輪子被稱為‘圓盤’(orbiculus)。事實上,流動的海洋以環狀圍繞在它的外圍。陸地被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叫亞洲,第二部分叫歐洲,第三部分叫非洲。”在伊西多爾看來,歐亞非三部分分別對應挪亞三個兒子的領地。
與古希臘羅馬時期相比,“陸地三分說”觀念在中世紀歐洲有了新發展。首先,加入閃、含、雅弗,並與亞非歐三大洲形成直接對應。在T-O地圖的世界呈現中,T嵌在O之中,O象徵著環繞陸地的海洋,T代表著把陸地分為三部分的三條主要水道,構成三大洲的分界線,即地中海(歐洲與非洲之間)、頓河(歐洲與亞洲之間)與尼羅河(非洲和亞洲之間)。
其次,認為亞洲面積最大,是歐洲和非洲面積之和。在古希臘人的“陸地三分說”觀念中,通常認為歐洲的面積是亞洲和利比亞的總和;而在中世紀基督教觀念中,亞洲通常單獨佔據地圖上半部分,歐洲和非洲合起來佔據下半部分(各佔1/4)。亞洲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面積上,還由於它是《聖經》諸多場景的所在地,伊甸園、亞拉臘山、耶路撒冷等都位於亞洲。前往東方的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朝聖,是中世紀基督徒的一項傳統。
再次,就地圖方位而言,與古希臘人通常以北方作為上方位不同,中世紀世界地圖一般把東方置於地圖上端。這主要借鑑了猶太人的做法,在希伯來語中,“北方”( )和“南方”(
)和“南方”( )分別代表著左和右,暗示東方為上的思想。東方(亞洲)位於上方位還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因為在基督教觀念中,東方作為天堂伊甸園的所在地,象徵著光明和生機。
最後,世界的中心不再是愛琴海地區,而是基督教聖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作為世界中心的觀念來自猶太人,“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她的四圍”。該觀念後來被中世紀基督教繼承,並進行符合基督教神學的解讀,耶路撒冷通常被描繪為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中心點。
現存的絕大多數中世紀地圖不是為旅行設計的,而是體現了基督徒對世界的理解,地圖上佈滿密密麻麻的點、線和座標,描繪了基督徒的希望與恐懼,代表著“救贖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alvation)。儘管中世紀的世界地圖不太關注地理的準確性,更多強調歷史和宗教信息的傳遞,但其中清楚地強調歐亞非三大洲及其區分,並與挪亞三個兒子的領地對應起來,體現在中世紀歐洲眾多的歷史、宗教、地理、文學等文獻中,表明“三大洲”觀念在當時已成為被人們廣泛接受的地理知識。13世紀英國教會作家巴託羅繆(Bartholomaeus Anglicus)寫道:“正如伊西多爾所說,世界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亞洲,第二部分是歐洲,第三部分是非洲。古人是這樣劃分的,但這三個部分並不均等,因為亞洲單獨佔世界一半,歐洲和非洲加起來佔世界另一半。如果把世界從東到西分成兩半,會發現亞洲在一邊,歐洲和非洲在另一邊。大洪水過後,挪亞的三個兒子分別統治著世界的三個部分:閃及其後代在亞洲,雅弗及其後代在歐洲,含及其後代在非洲。”
到15世紀末,隨著“地理大發現”的開展,歐洲航海家在歐亞非三大洲之外“發現”了新大陸,傳統的“陸地三分說”逐漸被修正。哥倫布從不認為他到達了一塊新大陸,而主張它是亞洲的一部分,即“印度”;但人們很快發現這是一塊完全獨立的大陸,不久以意大利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命名。雖然在世界地理中增加了美洲和澳洲等其他大洲,但歐亞非的基本框架和地理範圍維持下來,成為現代世界地理知識體系的基石。這種夾雜了想象和偏見的地理知識,藉助歐洲的軍事擴張和文化霸權,滲透到人們的區域身份和世界認知中,參與塑造歐洲和非歐洲地區的歷史,從而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陸地三分說”把已知世界人為劃分為歐亞非三部分,代表了以歐洲為中心認知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其實質是為了區分自我(歐洲)與“他者”(非歐洲)。在自我和“他者”的世界二分法下,歐洲自視為文明和先進的一方,非歐洲則是野蠻和落後的另一方。“西方”和“東方”是歐洲人認知和劃分世界的另一組概念,它與洲際劃分相結合,形成歐洲即“西方”、非歐洲即“東方”的刻板印象。源自閃語的“東方”一詞起初並無負面意義,但在洲際劃分基礎上,歐洲人把自我等同於西方,將“東方”視為“他者”,對“東方”予以負面解讀。在歐洲的異域想象中,“東方”通常被描繪為野蠻人和異教徒的聚居地,希羅多德、老普林尼等古典作家認為,東方居住著狗頭人、胸前長著五官的無頭人、單腿或四條腿的人以及其他樣貌怪異的半人半獸狀邪惡生物。這種帶有偏見的“東方”形象長期存在於歐洲人的觀念和話語中,並在相當程度上導致對外部世界的傲慢態度。
歐洲以洲際想象為中心的世界認知與古希臘的野蠻人觀念密切相關。古希臘人把世界人群分為兩大類別:希臘人(Hellenes)和野蠻人(barbaroi),來自亞洲和利比亞“邊緣地區”的野蠻人構成希臘人的“鏡子”,即非我族類的負面類型。然而,粗略統計創造和使用洲際概念的古希臘地理學家出生地,不少人並非出生於希臘本土或所謂歐洲地區,而是來自小亞細亞沿岸的希臘城邦。那些身處“亞洲”的希臘人處於異族強國(例如呂底亞和波斯帝國)頻繁威脅之下,使之對身份認同高度敏感,因此通過創造不同洲際概念來明確自己的文化身份。作為參照物,外部“他者”幫助歐洲建構了洲際身份和理想的自我形象。從古希臘開始,亞洲被視為主要的外部“威脅”,幾乎是歐洲永恆的“他者”。古羅馬學者瓦羅把亞洲定義為“所有不是歐洲的東西”,“正如所有的自然都分為天空和大地一樣,參照天空的區域,大地也分為亞洲和歐洲”。從歐洲的角度看,亞洲作為想象的對立面,並非由於它具有明確的特性,其存在的價值不過是用於襯托歐洲的“優越性”。
作為一種洲際身份認同,歐洲人的自我認識是一個不斷清晰的過程。在歷史上,所謂“歐洲”並非一個固定的地理空間,起初它的範圍僅限於愛琴海西岸地區,而後逐步向西向北擴展,羅馬軍事擴張和基督教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開始,歐洲與希臘的範圍並不明確,歐洲有時包括希臘,有時僅指希臘北部接壤地區(不含希臘)。進入羅馬帝國時代,整個希臘地區被併入羅馬版圖,希臘獨立於歐洲的觀念逐漸消除,藉助於羅馬的軍事擴張,歐洲的範圍擴大到帝國西部地區。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開始被用來指稱西部教會轄區。在中世紀早期拉丁語文獻中,“歐洲”一詞出現頻率較低。732年,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率軍在普瓦提埃戰役中打敗阿拉伯軍隊,成功阻止後者越過比利牛斯山,該事件被當時的編年史家視為“歐洲人”(Europeenses)的勝利。到800年,加冕後的查理曼被稱為“歐洲之王和歐洲之父”(rex,pater Europae )。在加洛林時期,歐洲通常指法蘭西、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核心區域,北歐、西北歐、東歐絕大部分地區尚未納入歐洲的地理範疇,這些地區的居民也不認為自己是歐洲人。10—12世紀,歐洲經歷“歐洲化”過程,既是宗教信仰層面的基督教化,更是地理身份層面的“歐洲化”,即原先缺乏歐洲身份認同的人開始明確認同歐洲並自稱歐洲人的過程。到1300年左右,“歐洲”已成為被廣泛認同的地理區域和文化身份。從但丁和彼特拉克等人的作品中看到,詩人但丁在其拉丁語著作中13次提及“歐洲”一詞,彼特拉克對該詞的使用更為頻繁。
此外,歐洲的洲際身份塑造需要來自外部“他者”的刺激。古典作家習慣把希臘人與波斯人的衝突,抽象化為“歐洲”與“亞洲”的敵對。希羅多德在總結希臘人和波斯人長達幾個世紀的宿怨時寫道,“波斯人聲稱亞細亞以及居住在那裡的外國人都是屬於他們的,但歐羅巴和希臘民族是與他們迥然不同的”。隨著阿拉伯帝國在東方的崛起,歐洲人認為自己面臨著強大且具有威脅性的“他者”,即伊斯蘭教不斷向西擴張。“十字軍東征”是促成歐洲認同發展的重要事件。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渲染”外部威脅,呼籲保衛歐洲免遭穆斯林入侵,“歐洲是世界的第三部分,我們基督徒只生活在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們世界的這一小部分受到突厥人和撒拉遜人的戰爭威脅。三百年前,他們征服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現在,他們企圖吞併歐洲其餘地區”。
到14、15世紀,來自東方的“威脅”進一步刺激歐洲人的洲際身份認同。奧斯曼人的西侵不僅規模龐大,而且持續時間更久,特別是1453年存在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人滅亡,引起歐洲社會極大恐慌。在許多歐洲人看來,拜占庭帝國滅亡導致“基督教歐洲”(Christian Europe )和“穆斯林亞洲”(Muslim Asia)之間形成明確區分。基督教歐洲通常把穆斯林描繪為邪惡、恐怖的“他者”,通過貶低對手以塑造理想的自我形象:“西方需要構建一個關於穆斯林的‘他者’形象,這是一個主導前現代關於伊斯蘭教話語的雙重過程。一方面,它創造出完全陌生和邪惡的撒拉遜人、摩爾人和突厥人形象……另一方面,這種明顯錯誤印象的產生使西方基督徒得以界定自我。從某種意義上說,穆斯林成了理想基督徒自我認知的反面形象,這種理想認知把歐洲人描繪成英勇、高尚、信奉真神和純正信仰的人。通過貶低對手,西方基督徒提升了自我形象,並在面對力量更強大、文化更成熟的敵人時試圖建立自信。”
“陸地三分說”既是歐洲對已知世界的認知和想象,也代表一種權力秩序。歐洲人根據“文明”程度的差異,把已知世界的不同區域劃分為若干等級,歐洲位於該等級體系的頂端,亞洲和非洲的重要性依次降低,從而形成“洲際等級體系”(continental hierarchy)。洲際等級觀念源自古希臘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希臘人所在的愛琴海地區為中心,距離中心越遠就越野蠻,從大地中心到邊緣的旅行是一場從文明到野蠻的穿越。學者卡普蘭指出,“當希臘人努力理解與他們接觸的民族和地區時,遂形成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它把希臘人與野蠻人區分開來,並將世界在空間上組織成不同的單位,即洲……各種各樣具有獨特習俗的民族被分配到其中”。夾雜著文化想象和誤讀的希臘中心主義(Hellenocentrism),把文明程度與地理位置聯繫起來,成為“證明”希臘人“優越性”的手段。古羅馬人沿襲自我中心主義,把羅馬城視為世界的中心,通過修築密集的道路網絡通向羅馬所征服的各個地區,並賦予居住在帝國邊陲的民族以蠻族身份。作為歐洲中心主義的前身,古希臘羅馬人的自我中心主義直接影響了後世歐洲人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認知,衍生出所謂“文明”和“野蠻”的世界二分法,成為其文化自信和心理優越感的源頭。
由於早期基督教的亞洲淵源,亞洲的重要性在古代晚期一度有所上升,例如奧古斯丁、伊西多爾等都強調亞洲的重要地位,亞洲取代歐洲在T-O地圖中佔據上半部分的關鍵位置等。但這種情況由於伊斯蘭教在亞洲的崛起逐漸發生了改變,到中世紀中後期,基督教勢力基本退回到歐洲範圍內,歐洲逐漸與“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的範疇重合。在歐洲中心主義思想影響下,不少基督教學者從《聖經》中尋找歐洲優於其他洲的依據,貶低東方(亞洲),抬高西方(歐洲)。在中世紀歐洲,洲際等級體系結合《聖經》對閃、含、雅弗的不同評判,從神學層面為歐洲中心主義提供支撐:歐洲是雅弗及其後裔的大陸,是基督徒的大陸;作為閃及其後裔居住地的亞洲,雖然有著輝煌的過去,但被置於歐洲之下的從屬地位,加上東方民族的固有屬性,已陷於停滯和野蠻狀態;非洲大陸的情況更為糟糕,他們作為含的後裔被判作其兄弟後裔的奴隸,淪為所謂的“黑暗大陸”(Dark Continent)。
可以說,蘊含等級觀念的洲際劃分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下的權力秩序,歐洲自視為世界的中心,認為這種中心既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基於此,洲際劃分是一種使歐洲凌駕於其他地區之上的方式,強調歐洲與非歐洲之間的區分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不同,更是文明程度的差異。具體來說,洲際劃分在地理環境和政治制度兩個層面,建構了所謂的“歐洲優越論”敘事。
一方面,從各大洲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出發,強調歐洲與非歐洲在氣候、風俗、人種等方面的差異性,人為論斷所謂歐洲“優越”而非歐洲“低劣”。希羅多德認為,希臘人內在傾向自由,而野蠻人傾向被奴役和被統治,原因是不同民族性格由不同的土地所孕育,嚴酷的氣候造就堅韌和熱愛自由的希臘人。希波克拉底從氣候環境對人類身體和性格的影響出發,認為歐洲優越於亞洲的原因是:歐洲寒冷多變的氣候條件使其居民勇猛和自由,而亞洲和非洲的炎熱氣候帶來疲乏和專制。亞里士多德更進一步,認為希臘位於最理想的中間地帶,“既具熱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有資格“治理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這種“環境決定論”把不同地區人群之間的差異歸因於自然條件,從而“確定”歐洲優於非歐洲地區乃客觀環境所致。
另一方面,不尊重各地政治文化的差異性,認為歐洲是文明程度最高和治理最好的地方,虛構出歐洲“自由”而非歐洲“專制”的神話。從希羅多德、埃斯庫羅斯等古典作家開始,波斯(亞洲)“專制”而希臘(歐洲)“自由”的形象就已確立起來,波斯君主政體被視為專制主義的代表和亞洲典型的政治統治模式。在歐洲中心主義話語下,歐洲人把東方(亞洲)等同於“專制”,製造出“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刻板印象。此霸權話語引申出來的邏輯是:歐洲自誕生起就優越於其他地區,歐洲作為文明的最高代表是其他地區的標杆和模範,“歐洲之所以對世界其他地區保持領先地位,是因為人類的思想在這裡取得了最大進步”。歐洲人自詡掌握了人類發展方向的“制高點”,強調由於非歐洲人的野蠻屬性,自己無法發展出高度發達的文明,所以需要歐洲人來改造,從而賦予歐洲人統治其他人的“正當性”。古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寫道:“沒錯,希臘人應當統治野蠻人,而不是野蠻人統治希臘人……他們是奴隸,而我們是生來自由的人。”
從本質上看,“陸地三分說”作為歐洲中心主義對已知世界的認知和想象,並非客觀公正的劃分,它把文明與野蠻、自由與專制之間的二元對立以及等級觀念,投射到歐洲、亞洲和非洲及其民族身上,構成所謂“歐洲優越論”的邏輯起點。洲際劃分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在看似合理的表面背後暗含著不同文明和價值觀的優劣對比,從而為“歐洲優越論”製造“合法性”基礎,確立歐洲對非歐洲的文化自信和心理優勢,作為攻擊和否定非歐洲地區的依據。
在前現代時期,所謂“歐洲優越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幻覺。與同一時期的亞洲、非洲相比,歐洲在許多方面並不先進,更不優越,甚至歐洲的文化也非原創。從源頭上說,古希臘和歐洲的文明要麼來自非歐洲地區,要麼受到後者的深刻影響,並在發展過程中與非歐洲地區存在密切交流和互鑑。東地中海地區歷來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前沿,中世紀歐洲文明持續受到歐洲以外地區(如中國、印度和阿拉伯)的滋養和影響。例如,“歐洲”的名字源自一個被誘拐的亞洲女性(歐羅巴);希臘早期文明的創造者是來自西亞和中亞的古印歐人,古希臘的語言、文化、醫學、科學等深受埃及和兩河流域等地的影響;主導中世紀歐洲精神世界的基督教發源於亞洲;揭開近代歐洲序幕的文藝復興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文化傳入的結果。學者馬丁·貝爾納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中指出,作為歐洲文明之根的古希臘文明,其根源要追溯到亞洲和非洲,它本身深受東方(尤其是埃及和閃語地區)的影響。可以說,並不存在一個完全孤立的歐洲文明,歐洲的發展是由歐洲和非歐洲地區共同推動的。然而,為確立對“他者”的優越性,歐洲人通過對“亞洲起源的失憶”(amnesia of her Asian origins),否定自身的東方起源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外來元素,建構起發端於古希臘羅馬、經中世紀基督教傳遞接力、再到近代文藝復興的單一線性敘事,其根基是一個排外的、理想化的古希臘文明。
人類居住的藍色星球是一個橢圓形球體,從海陸分佈和地質構造看,傳統上被稱為“舊大陸”的歐亞非大陸(Afro-Eurasia)是一個連續的地理整體,俗稱“世界島”,歐洲只是這塊大陸向西北方向伸出的半島狀陸地,法國詩人保羅·瓦萊裡曾把歐洲稱作“亞洲大陸的小岬角”。古希臘人在地理知識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對已知世界進行劃分,不僅把每個大洲內部想象為同質,誇大各大洲之間的差異性,而且帶有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過分突出歐洲的“優越性”,貶低非歐洲的地位。實際上,前現代時期的非歐洲人也有自己的世界劃分辦法,他們基本從未使用“亞細亞”或“阿非利加”的概念,更不接受所謂的野蠻人觀念。然而,到了近代,在歐洲的強勢擴張和話語霸權下,非歐洲地區的世界認知淪為邊緣性話語而被忽略乃至被遺忘。由於被納入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非歐洲地區經歷了“自我東方化”過程,儘管他們不熟悉也不願接受強加給自己的洲際身份界定(實際是外來的身份認同),這印證了馬克思的名言: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鑑於洲際話語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歷來有不少學者試圖加以突破。例如,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主張以文明為單位重新劃分世界,他歸納了歷史上出現過的26種文明形態,構成所謂“文明區域”概念:埃及、蘇美爾、中國、印度、猶太、西方、拜占庭、伊斯蘭、俄羅斯等,這是對傳統洲際概念的突破。但是,湯因比提出的文明區域過於零碎和龐雜而不便使用。1997年,地理學家馬丁·路易斯和歷史學者卡倫·魏根發表《大陸的神話:元地理學批判》,強調“洲”的概念是一種元地理學神話,提出重新劃分為10個“世界區域”,例如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拉丁美洲、歐洲、俄羅斯和東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這一觀點挑戰了傳統的洲際劃分辦法,但仍在使用帶有歐洲色彩的洲際話語和範疇。此外,關於世界區域的重新劃分,非歐洲地區並非完全處於“失語”狀態,也有若干嘗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批判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基礎上,依附論學者提出“中心—外圍”理論,毛澤東提出著名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在剖析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根源基礎上,闡發對世界劃分的非歐洲中心論理解,在亞非拉世界產生較大影響。
需要明確的是,目前廣為接受的洲際話語體系並非中立的概念,它本身即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是歐洲人兩千多年來認知和想象已知世界的“元概念”,更是歐洲霸權在地理領域的重要象徵。以歐亞非為代表的洲際話語的使用和推廣,反映的是歐洲(及其前身古希臘)對區域劃分和世界認知的話語主導權,通過權力與知識的聯手,使歐洲標準成為世界標準,其目的是使歐洲和西方凌駕於其他地區之上。在歐洲人的話語運作和權力操控下,非歐洲地區的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接受了歐洲“製造”的地理框架,被迫戴著“歐洲中心論”的有色眼鏡審視自己和觀察世界。作為被非歐洲地區沿用近五百年的地理話語和身份認同,歐亞非等洲際劃分已經滲透到當地民眾的思想意識和文化習慣中,想要撼動絕非易事。很顯然,用歐洲製造的洲際話語來破除“歐洲中心論”是不現實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尋找一種更為客觀中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替代性世界區域劃分概念,具有不容忽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也是區域研究今後應當努力的方向。
《歷史研究》在線投稿系統已於2021年9月15日啟用,網址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點擊下方“閱讀原文”,關注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官方微店,訂閱《歷史研究》《歷史評論》和《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
)分別代表著左和右,暗示東方為上的思想。東方(亞洲)位於上方位還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因為在基督教觀念中,東方作為天堂伊甸園的所在地,象徵著光明和生機。
最後,世界的中心不再是愛琴海地區,而是基督教聖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作為世界中心的觀念來自猶太人,“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將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國都在她的四圍”。該觀念後來被中世紀基督教繼承,並進行符合基督教神學的解讀,耶路撒冷通常被描繪為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中心點。
現存的絕大多數中世紀地圖不是為旅行設計的,而是體現了基督徒對世界的理解,地圖上佈滿密密麻麻的點、線和座標,描繪了基督徒的希望與恐懼,代表著“救贖的地理”(Geographies of Salvation)。儘管中世紀的世界地圖不太關注地理的準確性,更多強調歷史和宗教信息的傳遞,但其中清楚地強調歐亞非三大洲及其區分,並與挪亞三個兒子的領地對應起來,體現在中世紀歐洲眾多的歷史、宗教、地理、文學等文獻中,表明“三大洲”觀念在當時已成為被人們廣泛接受的地理知識。13世紀英國教會作家巴託羅繆(Bartholomaeus Anglicus)寫道:“正如伊西多爾所說,世界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亞洲,第二部分是歐洲,第三部分是非洲。古人是這樣劃分的,但這三個部分並不均等,因為亞洲單獨佔世界一半,歐洲和非洲加起來佔世界另一半。如果把世界從東到西分成兩半,會發現亞洲在一邊,歐洲和非洲在另一邊。大洪水過後,挪亞的三個兒子分別統治著世界的三個部分:閃及其後代在亞洲,雅弗及其後代在歐洲,含及其後代在非洲。”
到15世紀末,隨著“地理大發現”的開展,歐洲航海家在歐亞非三大洲之外“發現”了新大陸,傳統的“陸地三分說”逐漸被修正。哥倫布從不認為他到達了一塊新大陸,而主張它是亞洲的一部分,即“印度”;但人們很快發現這是一塊完全獨立的大陸,不久以意大利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命名。雖然在世界地理中增加了美洲和澳洲等其他大洲,但歐亞非的基本框架和地理範圍維持下來,成為現代世界地理知識體系的基石。這種夾雜了想象和偏見的地理知識,藉助歐洲的軍事擴張和文化霸權,滲透到人們的區域身份和世界認知中,參與塑造歐洲和非歐洲地區的歷史,從而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陸地三分說”把已知世界人為劃分為歐亞非三部分,代表了以歐洲為中心認知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其實質是為了區分自我(歐洲)與“他者”(非歐洲)。在自我和“他者”的世界二分法下,歐洲自視為文明和先進的一方,非歐洲則是野蠻和落後的另一方。“西方”和“東方”是歐洲人認知和劃分世界的另一組概念,它與洲際劃分相結合,形成歐洲即“西方”、非歐洲即“東方”的刻板印象。源自閃語的“東方”一詞起初並無負面意義,但在洲際劃分基礎上,歐洲人把自我等同於西方,將“東方”視為“他者”,對“東方”予以負面解讀。在歐洲的異域想象中,“東方”通常被描繪為野蠻人和異教徒的聚居地,希羅多德、老普林尼等古典作家認為,東方居住著狗頭人、胸前長著五官的無頭人、單腿或四條腿的人以及其他樣貌怪異的半人半獸狀邪惡生物。這種帶有偏見的“東方”形象長期存在於歐洲人的觀念和話語中,並在相當程度上導致對外部世界的傲慢態度。
歐洲以洲際想象為中心的世界認知與古希臘的野蠻人觀念密切相關。古希臘人把世界人群分為兩大類別:希臘人(Hellenes)和野蠻人(barbaroi),來自亞洲和利比亞“邊緣地區”的野蠻人構成希臘人的“鏡子”,即非我族類的負面類型。然而,粗略統計創造和使用洲際概念的古希臘地理學家出生地,不少人並非出生於希臘本土或所謂歐洲地區,而是來自小亞細亞沿岸的希臘城邦。那些身處“亞洲”的希臘人處於異族強國(例如呂底亞和波斯帝國)頻繁威脅之下,使之對身份認同高度敏感,因此通過創造不同洲際概念來明確自己的文化身份。作為參照物,外部“他者”幫助歐洲建構了洲際身份和理想的自我形象。從古希臘開始,亞洲被視為主要的外部“威脅”,幾乎是歐洲永恆的“他者”。古羅馬學者瓦羅把亞洲定義為“所有不是歐洲的東西”,“正如所有的自然都分為天空和大地一樣,參照天空的區域,大地也分為亞洲和歐洲”。從歐洲的角度看,亞洲作為想象的對立面,並非由於它具有明確的特性,其存在的價值不過是用於襯托歐洲的“優越性”。
作為一種洲際身份認同,歐洲人的自我認識是一個不斷清晰的過程。在歷史上,所謂“歐洲”並非一個固定的地理空間,起初它的範圍僅限於愛琴海西岸地區,而後逐步向西向北擴展,羅馬軍事擴張和基督教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開始,歐洲與希臘的範圍並不明確,歐洲有時包括希臘,有時僅指希臘北部接壤地區(不含希臘)。進入羅馬帝國時代,整個希臘地區被併入羅馬版圖,希臘獨立於歐洲的觀念逐漸消除,藉助於羅馬的軍事擴張,歐洲的範圍擴大到帝國西部地區。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歐洲開始被用來指稱西部教會轄區。在中世紀早期拉丁語文獻中,“歐洲”一詞出現頻率較低。732年,法蘭克王國宮相查理·馬特率軍在普瓦提埃戰役中打敗阿拉伯軍隊,成功阻止後者越過比利牛斯山,該事件被當時的編年史家視為“歐洲人”(Europeenses)的勝利。到800年,加冕後的查理曼被稱為“歐洲之王和歐洲之父”(rex,pater Europae )。在加洛林時期,歐洲通常指法蘭西、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核心區域,北歐、西北歐、東歐絕大部分地區尚未納入歐洲的地理範疇,這些地區的居民也不認為自己是歐洲人。10—12世紀,歐洲經歷“歐洲化”過程,既是宗教信仰層面的基督教化,更是地理身份層面的“歐洲化”,即原先缺乏歐洲身份認同的人開始明確認同歐洲並自稱歐洲人的過程。到1300年左右,“歐洲”已成為被廣泛認同的地理區域和文化身份。從但丁和彼特拉克等人的作品中看到,詩人但丁在其拉丁語著作中13次提及“歐洲”一詞,彼特拉克對該詞的使用更為頻繁。
此外,歐洲的洲際身份塑造需要來自外部“他者”的刺激。古典作家習慣把希臘人與波斯人的衝突,抽象化為“歐洲”與“亞洲”的敵對。希羅多德在總結希臘人和波斯人長達幾個世紀的宿怨時寫道,“波斯人聲稱亞細亞以及居住在那裡的外國人都是屬於他們的,但歐羅巴和希臘民族是與他們迥然不同的”。隨著阿拉伯帝國在東方的崛起,歐洲人認為自己面臨著強大且具有威脅性的“他者”,即伊斯蘭教不斷向西擴張。“十字軍東征”是促成歐洲認同發展的重要事件。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渲染”外部威脅,呼籲保衛歐洲免遭穆斯林入侵,“歐洲是世界的第三部分,我們基督徒只生活在其中的一小部分!……我們世界的這一小部分受到突厥人和撒拉遜人的戰爭威脅。三百年前,他們征服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島;現在,他們企圖吞併歐洲其餘地區”。
到14、15世紀,來自東方的“威脅”進一步刺激歐洲人的洲際身份認同。奧斯曼人的西侵不僅規模龐大,而且持續時間更久,特別是1453年存在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被奧斯曼人滅亡,引起歐洲社會極大恐慌。在許多歐洲人看來,拜占庭帝國滅亡導致“基督教歐洲”(Christian Europe )和“穆斯林亞洲”(Muslim Asia)之間形成明確區分。基督教歐洲通常把穆斯林描繪為邪惡、恐怖的“他者”,通過貶低對手以塑造理想的自我形象:“西方需要構建一個關於穆斯林的‘他者’形象,這是一個主導前現代關於伊斯蘭教話語的雙重過程。一方面,它創造出完全陌生和邪惡的撒拉遜人、摩爾人和突厥人形象……另一方面,這種明顯錯誤印象的產生使西方基督徒得以界定自我。從某種意義上說,穆斯林成了理想基督徒自我認知的反面形象,這種理想認知把歐洲人描繪成英勇、高尚、信奉真神和純正信仰的人。通過貶低對手,西方基督徒提升了自我形象,並在面對力量更強大、文化更成熟的敵人時試圖建立自信。”
“陸地三分說”既是歐洲對已知世界的認知和想象,也代表一種權力秩序。歐洲人根據“文明”程度的差異,把已知世界的不同區域劃分為若干等級,歐洲位於該等級體系的頂端,亞洲和非洲的重要性依次降低,從而形成“洲際等級體系”(continental hierarchy)。洲際等級觀念源自古希臘的自我中心主義,以希臘人所在的愛琴海地區為中心,距離中心越遠就越野蠻,從大地中心到邊緣的旅行是一場從文明到野蠻的穿越。學者卡普蘭指出,“當希臘人努力理解與他們接觸的民族和地區時,遂形成一種獨特的世界觀,它把希臘人與野蠻人區分開來,並將世界在空間上組織成不同的單位,即洲……各種各樣具有獨特習俗的民族被分配到其中”。夾雜著文化想象和誤讀的希臘中心主義(Hellenocentrism),把文明程度與地理位置聯繫起來,成為“證明”希臘人“優越性”的手段。古羅馬人沿襲自我中心主義,把羅馬城視為世界的中心,通過修築密集的道路網絡通向羅馬所征服的各個地區,並賦予居住在帝國邊陲的民族以蠻族身份。作為歐洲中心主義的前身,古希臘羅馬人的自我中心主義直接影響了後世歐洲人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認知,衍生出所謂“文明”和“野蠻”的世界二分法,成為其文化自信和心理優越感的源頭。
由於早期基督教的亞洲淵源,亞洲的重要性在古代晚期一度有所上升,例如奧古斯丁、伊西多爾等都強調亞洲的重要地位,亞洲取代歐洲在T-O地圖中佔據上半部分的關鍵位置等。但這種情況由於伊斯蘭教在亞洲的崛起逐漸發生了改變,到中世紀中後期,基督教勢力基本退回到歐洲範圍內,歐洲逐漸與“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的範疇重合。在歐洲中心主義思想影響下,不少基督教學者從《聖經》中尋找歐洲優於其他洲的依據,貶低東方(亞洲),抬高西方(歐洲)。在中世紀歐洲,洲際等級體系結合《聖經》對閃、含、雅弗的不同評判,從神學層面為歐洲中心主義提供支撐:歐洲是雅弗及其後裔的大陸,是基督徒的大陸;作為閃及其後裔居住地的亞洲,雖然有著輝煌的過去,但被置於歐洲之下的從屬地位,加上東方民族的固有屬性,已陷於停滯和野蠻狀態;非洲大陸的情況更為糟糕,他們作為含的後裔被判作其兄弟後裔的奴隸,淪為所謂的“黑暗大陸”(Dark Continent)。
可以說,蘊含等級觀念的洲際劃分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下的權力秩序,歐洲自視為世界的中心,認為這種中心既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基於此,洲際劃分是一種使歐洲凌駕於其他地區之上的方式,強調歐洲與非歐洲之間的區分不僅是地理空間上的不同,更是文明程度的差異。具體來說,洲際劃分在地理環境和政治制度兩個層面,建構了所謂的“歐洲優越論”敘事。
一方面,從各大洲不同的自然地理條件出發,強調歐洲與非歐洲在氣候、風俗、人種等方面的差異性,人為論斷所謂歐洲“優越”而非歐洲“低劣”。希羅多德認為,希臘人內在傾向自由,而野蠻人傾向被奴役和被統治,原因是不同民族性格由不同的土地所孕育,嚴酷的氣候造就堅韌和熱愛自由的希臘人。希波克拉底從氣候環境對人類身體和性格的影響出發,認為歐洲優越於亞洲的原因是:歐洲寒冷多變的氣候條件使其居民勇猛和自由,而亞洲和非洲的炎熱氣候帶來疲乏和專制。亞里士多德更進一步,認為希臘位於最理想的中間地帶,“既具熱忱,也有理智;精神健旺,所以能永保自由”,有資格“治理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這種“環境決定論”把不同地區人群之間的差異歸因於自然條件,從而“確定”歐洲優於非歐洲地區乃客觀環境所致。
另一方面,不尊重各地政治文化的差異性,認為歐洲是文明程度最高和治理最好的地方,虛構出歐洲“自由”而非歐洲“專制”的神話。從希羅多德、埃斯庫羅斯等古典作家開始,波斯(亞洲)“專制”而希臘(歐洲)“自由”的形象就已確立起來,波斯君主政體被視為專制主義的代表和亞洲典型的政治統治模式。在歐洲中心主義話語下,歐洲人把東方(亞洲)等同於“專制”,製造出“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的刻板印象。此霸權話語引申出來的邏輯是:歐洲自誕生起就優越於其他地區,歐洲作為文明的最高代表是其他地區的標杆和模範,“歐洲之所以對世界其他地區保持領先地位,是因為人類的思想在這裡取得了最大進步”。歐洲人自詡掌握了人類發展方向的“制高點”,強調由於非歐洲人的野蠻屬性,自己無法發展出高度發達的文明,所以需要歐洲人來改造,從而賦予歐洲人統治其他人的“正當性”。古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得斯寫道:“沒錯,希臘人應當統治野蠻人,而不是野蠻人統治希臘人……他們是奴隸,而我們是生來自由的人。”
從本質上看,“陸地三分說”作為歐洲中心主義對已知世界的認知和想象,並非客觀公正的劃分,它把文明與野蠻、自由與專制之間的二元對立以及等級觀念,投射到歐洲、亞洲和非洲及其民族身上,構成所謂“歐洲優越論”的邏輯起點。洲際劃分體現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話語霸權,在看似合理的表面背後暗含著不同文明和價值觀的優劣對比,從而為“歐洲優越論”製造“合法性”基礎,確立歐洲對非歐洲的文化自信和心理優勢,作為攻擊和否定非歐洲地區的依據。
在前現代時期,所謂“歐洲優越論”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幻覺。與同一時期的亞洲、非洲相比,歐洲在許多方面並不先進,更不優越,甚至歐洲的文化也非原創。從源頭上說,古希臘和歐洲的文明要麼來自非歐洲地區,要麼受到後者的深刻影響,並在發展過程中與非歐洲地區存在密切交流和互鑑。東地中海地區歷來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前沿,中世紀歐洲文明持續受到歐洲以外地區(如中國、印度和阿拉伯)的滋養和影響。例如,“歐洲”的名字源自一個被誘拐的亞洲女性(歐羅巴);希臘早期文明的創造者是來自西亞和中亞的古印歐人,古希臘的語言、文化、醫學、科學等深受埃及和兩河流域等地的影響;主導中世紀歐洲精神世界的基督教發源於亞洲;揭開近代歐洲序幕的文藝復興很大程度上是阿拉伯文化傳入的結果。學者馬丁·貝爾納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亞非之根》中指出,作為歐洲文明之根的古希臘文明,其根源要追溯到亞洲和非洲,它本身深受東方(尤其是埃及和閃語地區)的影響。可以說,並不存在一個完全孤立的歐洲文明,歐洲的發展是由歐洲和非歐洲地區共同推動的。然而,為確立對“他者”的優越性,歐洲人通過對“亞洲起源的失憶”(amnesia of her Asian origins),否定自身的東方起源以及發展過程中的外來元素,建構起發端於古希臘羅馬、經中世紀基督教傳遞接力、再到近代文藝復興的單一線性敘事,其根基是一個排外的、理想化的古希臘文明。
人類居住的藍色星球是一個橢圓形球體,從海陸分佈和地質構造看,傳統上被稱為“舊大陸”的歐亞非大陸(Afro-Eurasia)是一個連續的地理整體,俗稱“世界島”,歐洲只是這塊大陸向西北方向伸出的半島狀陸地,法國詩人保羅·瓦萊裡曾把歐洲稱作“亞洲大陸的小岬角”。古希臘人在地理知識尚不完備的情況下對已知世界進行劃分,不僅把每個大洲內部想象為同質,誇大各大洲之間的差異性,而且帶有強烈的自我中心主義,過分突出歐洲的“優越性”,貶低非歐洲的地位。實際上,前現代時期的非歐洲人也有自己的世界劃分辦法,他們基本從未使用“亞細亞”或“阿非利加”的概念,更不接受所謂的野蠻人觀念。然而,到了近代,在歐洲的強勢擴張和話語霸權下,非歐洲地區的世界認知淪為邊緣性話語而被忽略乃至被遺忘。由於被納入歐洲主導的世界體系,非歐洲地區經歷了“自我東方化”過程,儘管他們不熟悉也不願接受強加給自己的洲際身份界定(實際是外來的身份認同),這印證了馬克思的名言: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鑑於洲際話語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歷來有不少學者試圖加以突破。例如,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主張以文明為單位重新劃分世界,他歸納了歷史上出現過的26種文明形態,構成所謂“文明區域”概念:埃及、蘇美爾、中國、印度、猶太、西方、拜占庭、伊斯蘭、俄羅斯等,這是對傳統洲際概念的突破。但是,湯因比提出的文明區域過於零碎和龐雜而不便使用。1997年,地理學家馬丁·路易斯和歷史學者卡倫·魏根發表《大陸的神話:元地理學批判》,強調“洲”的概念是一種元地理學神話,提出重新劃分為10個“世界區域”,例如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拉丁美洲、歐洲、俄羅斯和東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這一觀點挑戰了傳統的洲際劃分辦法,但仍在使用帶有歐洲色彩的洲際話語和範疇。此外,關於世界區域的重新劃分,非歐洲地區並非完全處於“失語”狀態,也有若干嘗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批判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基礎上,依附論學者提出“中心—外圍”理論,毛澤東提出著名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在剖析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秩序根源基礎上,闡發對世界劃分的非歐洲中心論理解,在亞非拉世界產生較大影響。
需要明確的是,目前廣為接受的洲際話語體系並非中立的概念,它本身即是歐洲中心主義的產物,是歐洲人兩千多年來認知和想象已知世界的“元概念”,更是歐洲霸權在地理領域的重要象徵。以歐亞非為代表的洲際話語的使用和推廣,反映的是歐洲(及其前身古希臘)對區域劃分和世界認知的話語主導權,通過權力與知識的聯手,使歐洲標準成為世界標準,其目的是使歐洲和西方凌駕於其他地區之上。在歐洲人的話語運作和權力操控下,非歐洲地區的人們有意或無意地接受了歐洲“製造”的地理框架,被迫戴著“歐洲中心論”的有色眼鏡審視自己和觀察世界。作為被非歐洲地區沿用近五百年的地理話語和身份認同,歐亞非等洲際劃分已經滲透到當地民眾的思想意識和文化習慣中,想要撼動絕非易事。很顯然,用歐洲製造的洲際話語來破除“歐洲中心論”是不現實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尋找一種更為客觀中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替代性世界區域劃分概念,具有不容忽視的必要性與緊迫性,也是區域研究今後應當努力的方向。
《歷史研究》在線投稿系統已於2021年9月15日啟用,網址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點擊下方“閱讀原文”,關注中國社科院學術期刊官方微店,訂閱《歷史研究》《歷史評論》和《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