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主要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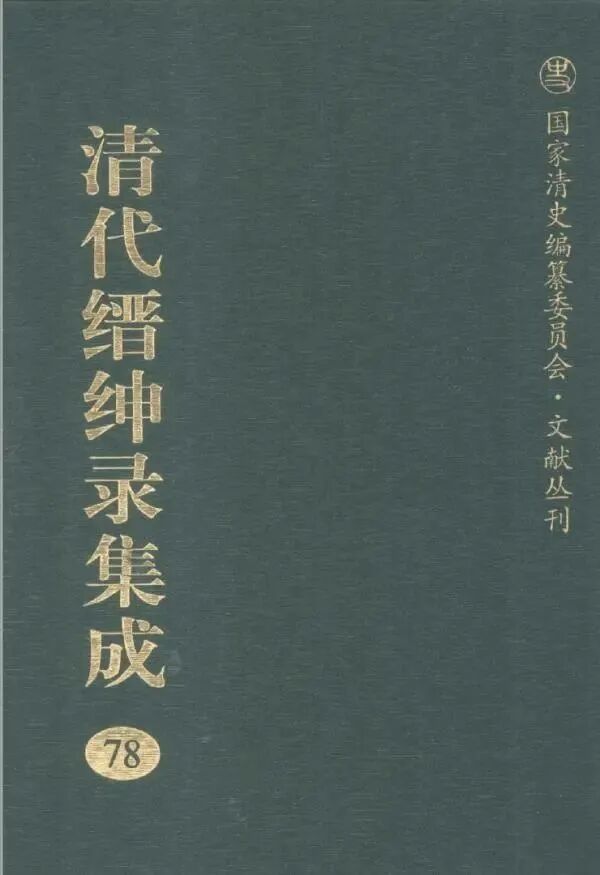
清史研究自1912年以來已走過百年曆程,特別是2002年國家清史纂修工程啟動以後,清史研究更加興盛,僅《清史書目(1911一2011)》收錄的清史著述就有四萬餘種,由中國知網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共建的《清史研究專題庫》收錄論文數(含學位論文)、報紙、工具書等共六十餘萬條(種)。在方法上,清史研究議題轉換迅速,新理論新方法層出不窮,經世致用空間廣闊,可以說清史研究已逐步改變了其在斷代史研究中的落後局面,走向繁榮。但與這一繁榮局面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傳統政治史的衰落。劉鳳雲曾論及世紀之交史學界發生的最大變化是政治史與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的易位,放棄了對重大理論的研究,忽視了國家與政府,特別是國家權力運作的研究,將政治史隱身於社會史之中,從而導致了政治史顯學地位的喪失。政治史研究地位的相對下降是史學界面臨的共性問題,而各個斷代政治史研究顯然還有很大差異,與中古史領域政治史研究積澱深厚且仍具有較強影響力不同,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衰落更為明顯,其背後具有一些特殊原因,那就是清史研究起步較晚,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逐漸走向繁榮,與上古史、中古史相比,政治史研究積累本身就比較薄弱,此時又恰逢社會史等新領域崛起,導致政治史研究“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研究方法也面臨材料枯燥、議題陳舊、解釋僵化等困境,難以提出具有籠罩性和輻射力的解釋框架。同時,清史研究領域史料豐富固然是一個優勢,但議題泛化導致缺少聚焦,對材料的解讀欠缺精細,同時無法窮盡佔有史料也難免方法論上“選精”與“集萃”之譏。
政治史研究的衰退特別是對於重大議題的疏離,自然也導致了一系列新的問題。關於史學議題的碎片化和短期主義早已引起學界廣泛討論,《近代史研究》曾專門組織過“碎片化”問題筆談,儘管學界同仁對這一趨勢看法不一,但對“碎片化”業已對史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一問題則無異議。喬·古爾迪(Jo Guldi)、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歷史學宣言》中更宣稱“一個幽靈,短期主義的幽靈,正困擾著我們這個時代”。作者認為這種“短期主義”史學的出現既與20世紀70年代以後年輕一代對於政治史的疏離、放棄宏觀敘事與道德規諫有關,也與史學內部面臨的激烈競爭導致史學專業化程度的加強有關。作者深信“短期主義”對史學的困擾不僅存在於英語世界,而且對其他語言地區也同樣適用。有鑑於此,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倡導政治史研究的迴歸與復興。楊念群早在2004年就提出要重提政治史研究,認為地方故事的脈絡替代不了“政治”在跨地區意義上的整合作用,並且要把“政治”當作一種相對獨立的運轉機制進行再研究。陳明明也認為社會史、文化史的“碎片化”和“地方化”敘事,畢竟代替不了政治在跨地區(整體上)和跨領域(制度上)層面的基礎性綜論,社會史、文化史“專業化”和“去中心化”取向也無法割除經濟、文化、社會生活同政治結構的相互依存關係。類似議論在唐代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反思中也有體現。
在政治史研究中,官僚體制是核心問題之一。那麼,官僚政治史如何再出發,近二十年來學界進行了諸多探索,特別是在深具政治史研究傳統的中古史領域。這些探索對於清代官僚政治史具有較強的借鑑價值,但學術發展“似我者死”,清代官僚政治史也需要利用自身獨特優勢,走出一條新路。
在官僚政治史特別是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後出現過多種研究理路,孫正軍對鄧小南倡導的“活”的制度史、閻步克主張的制度史觀以及侯旭東提倡的日常統治研究的觀察視角、研究取向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制度史觀對於長時段和結構的偏重,強調製度的主體性,實際是對制度所構成的較為穩定的“秩序”的重視。活的制度史、日常統治史研究取徑將關係、過程、行為引入制度史研究,如此一來,制度更多呈現出相對性、暫時性和不確定性的一面,可視為一種“混沌”。兩種維度的觀察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各具價值,需要在不同的研究對象和情景下選擇合適的研究視角。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意識到制度當中的“混沌”與“秩序”看似對立存在,但也是辯證的統一體。當面對個案等微觀層次時,制度往往呈現出較為不確定性的一面,而面對整體或長時段時,制度卻又常常呈現出有秩序和規律性的一面。可以說各類隨機現象背後同樣存在隱性規則,微觀系統的相互作用導致宏觀層面的系統結構與行為,譬如阿西莫夫在《基地》這本經典科幻小說中所幻想建立的心理史學,當人群規模超過150人時就可以預測群體行為。在這一方面,歷史學和經濟學、物理學並無本質不同,在微觀和宏觀層面上存在著不同的規則,處理不同層次的問題需要選擇不同的方法論。正是為了實現微觀與宏觀規律的統一性,才需要建立各類複雜系統(Complex Systems),如202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了“建立地球氣候的物理模型、量化其可變性並可靠地預測全球變暖”相關研究,主要就是表彰其對我們理解複雜物理系統的開創性貢獻。歷史學的研究也不例外,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同樣需要構建一套平衡“混沌”和“秩序”的複雜系統。
如果說當下的史學界通過大量微觀的、個案的、區域的研究呈現了大量“混沌”狀態的話,但如何從“混沌”出發進而引至對“結構”的分析,似乎尚不充分。社會科學在面臨這一問題時,通常有一些擴展個案研究的處理方式,如超越個案的概括、個案中的概括、分析性概括以及擴展個案方法,更重要的是定量方法的使用。不過史學界對於定量方法認可度一直不高,短暫興起的計量史學也很早就遭到史學界的批判,直到近年來才又重新引起關注。可以說,定量分析特別是概率和統計思維在史學研究中應用不足一直是史學研究的特點,有的學者將其視作人文學科區別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獨特魅力所在。這樣一來,必定會導致史學研究朝著微觀的方向愈來愈深入,在這裡歷史呈現了更多的無序性和非規律性,進而使得史學家一定程度上放棄了把握整體歷史的信心,喪失了藉助歷史規律經世致用的信念。而國家與社會對於歷史的需求顯然不僅僅止於瞭解細部的歷史,既然史學界弱化了這一研究取向,那麼自然就有社會科學的學者開始關注宏大歷史問題,歷史社會學、歷史政治學等應運而生,且往往強調其與歷史學研究的區別,如歷史政治學就強調其所追求的研究應當具有理論自覺而非如歷史學領域的政治史往往停留在史實考證與敘述層面。但對於宏觀歷史進程的把握,如果缺少足夠精確的經驗研究,理論自覺也具有脫離歷史事實的危險。因此,官僚政治史的研究要再出發,就需要吸納百家所長,既要處理好從制度主體出發所引致的不確定性,也要研究可以把握的制度結構與制度整體,更要在二者之間架設起一套複雜系統且能同時容納“混沌”與“秩序”。在這一官僚政治史的複雜系統中,既需要吸收制度史觀、活的制度史、日常統治史研究、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研究的長處,也需要引入計量分析等數字人文工具,將微觀分析與結構思維有機結合起來,史實考證、歷史敘述、理論自覺都可以容納進來,也許可以帶來官僚政治史研究的新意,而這也是中國古代史後半段和近現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優勢所在。“數字人文”正是可以在其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新方法。
數字人文的前身是人文計算,自2004年以後“數字人文”一詞開始流行,並進入飛速發展期,研究對象及方法更為多元,數字與人文融合更加深入。2015年以後數字人文逐漸在中國大陸地區成為研究熱點,至今不衰,業已對史學研究帶來較大沖擊和挑戰。迄今為止,數字人文的內涵與外延仍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
就清代官僚政治史而言,數字人文可以通過計量手段提供結構化思維。歷史學和社會科學一個較大的方法論的區別,用小威廉·H.休厄爾(William H.Sewell)《歷史的邏輯:社會理論與社會轉型》一書的總結,便是歷史學家滿足於多個不明確但最終在因果關係上相互交織的可能性,社會科學家則嘗試釐清在因果關係中最重要的環節並完整解釋他們系統性的動態,用清晰定義的結構性特徵解釋現象。結構性思維是社會科學中值得歷史學家迎頭趕上的長處。清代官僚政治史一個優勢就在於全樣本官僚信息的留存,“可以掌握研究對象的總體,進而為統計推斷帶來幫助”。這樣基於整體官僚結構的量化研究方法就有條件展開。
清史學界早已開始利用計量方法進行官僚政治與社會史的探究,如何炳棣的《明清社會史論》中就有諸如“省級及地方官員初任資格之百分比分佈”表格統計結果,只是當時還沒有條件掌握全樣本的數據,只能依賴片段的資料與統計作為歷史背景的輔助。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也曾根據《縉紳全書》等資料統計州縣官的種族、出身背景等。而魏秀梅利用《清季職官表》等工具書先後從量的角度探討過督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的人事嬗遞現象。對於基層地方官,目前最經典的研究是李國祁、周天生、許弘義的《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及王志明的《清代職官人事研究——基於引見官員履歷檔案的考證分析》。李國祁及其團隊在較為艱苦的條件下全面翻閱了省級通志4部、府志48部、州志(含直隸州)36部、縣誌349部,共計437部,設計了744張統計表,涵蓋知府4935人、直隸州知州2249人、散州知州4439人、知縣42602人,共計54225人。遺憾的是,這一成果只有一些研究結論以表格的形式公佈,缺少原始數據。王志明《清代職官人事研究——基於引見官員履歷檔案的考證分析》主要利用的是引見官履歷檔,涉及文官35597人,綠營武官4782人,八旗武官1199人,比較專門。此外,職官類的工具書編纂較多,質量也較高,但主要是查閱功能,無法滿足數字化環境的計量需求。現有數據庫如“清代職官資料庫”“人名權威人物傳記資料庫”等一般都建立在傳統工具書之上,資料經過考訂,準確性較高,不過大多偏重於高級官員,數量有限。總體而言,現有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工具書較侷限於高級官員或特定文獻如履歷檔中的官員,可以進行簡單的靜態統計,但數據不夠齊全,也無法滿足數字人文時代多樣化的計量需求。
近年來,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樣本數據整理取得了重大進展。《縉紳錄》量化數據庫受到清史學界越來越多的重視,這是由於《縉紳錄》量化數據庫的結構化程度較高,又是具有系統性和連續性的數據記錄,故而成為迄今為止清代官員最重要的數據寶庫,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一康文林研究團隊已在錄入數據並建設《縉紳錄》量化數據庫,1850—1864年、1901—1912年段數據業已在香港科技大學圖書館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數據共享平臺公開,研究論文也已陸續刊出。這一數據庫也引起經濟學、管理學等學界同仁的重視。但這一數據庫同樣面臨清代前期《縉紳錄》留存不足、記錄多為實授官員而署理官員缺失等一些根源於《縉紳錄》版本本身的問題,所以需要不同來源的官員數據進行補充、訂正。眾所周知,在當今中國所存地方誌中,以清代數量最為豐富,有六千餘部,加上民國方誌中對於清代官員的回溯性記錄,大體來說,範圍上涵蓋了全國各省,時間上從清初到清末,除了縣誌外,還有府志和省志,其中職官是必須記載的類目,這就意味著在地方誌中保存有大量系統而連續的職官信息,含實授、署理等多種類型,可以有效彌補《縉紳錄》量化數據庫的不足,從而能夠在兩個數據庫結合的基礎上,搭配其他相關資料,形成清代職官信息的全樣本數據。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在2021年啟動了“基於地方誌的清代職官信息集成數據庫”建設,正力爭早日完成。
與官僚信息相關的數據資源遠不止《縉紳錄》和地方誌,有待納入職官信息數據的資源還有很多,如履歷檔同樣是記錄官員出身和遷轉的非常重要的數據。此外,像鄉試錄、同官錄、硃卷及清代選官任官的奏疏中保留了大量官員個人信息,亦需被統一整合進入一個更大規模的職官信息數據集成系統之中。這樣一來,至少可以在三個層面上對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提供全新的視角:其一,不再僅侷限於對個別政治人物或政治派別的研究,而可以數十萬官員數據為基礎,對整體官僚政治結構進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歸納和分析。其二,不再僅侷限於高級官員,可以將中級、低級官員共同納入其中,官僚政治史的研究對象將更加全面和系統,也可以說有機會擺脫以上層政治和高級官員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範式。其三,利用數字人文方法將官僚信息、施政行為與氣候(雨雪分寸數據)、經濟(糧價數據:庫)、災害(清代災害信息集成數據庫)、地理(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等進行關聯,從而可望從整體和有機關聯的關係角度提供一種新的觀察歷史、解釋歷史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系統性史料的留存,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之前各代常常存在的缺乏系統性、數據不夠齊全等弊端,為數據庫的建設與計量方法的應用提供了相當優越的條件。這樣一來,融合清代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等多個側面的數據庫的互聯互通就為構建一套複雜系統提供了可能。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清代官僚信息的全樣本數據庫就將建成,至少在以下重大問題上提供新的研究可能。
第一,對官僚結構的整體計量分析,探索官僚體系的動態變化,研究王朝興衰的規律。有了全樣本數據的支撐,對於官僚結構的計量分析將為我們透視清代官僚體系的靜態與動態演變提供有力幫助。譬如官員實授與署理比例、出身、任職年齡、任職地域的動態演變,制度設計中如何兼顧穩定與效率,有助於探索官僚結構的變遷與王朝興衰的根本動力。通過計量結果可以發現新問題,特別是對於原來不夠引人注目的史料可能會有重新解讀。筆者先前曾經對晚清官員的出身做過計量分析,發現所謂晚清捐納帶給官員的衝擊並不體現在正印官如知府、知州、知縣上,就統計結果可知,晚清正印官群體出身進士和舉人等正途的比例反而有所增加,這就提醒我們需要重新閱讀《大清會典》等傳統典章制度文獻,體會到在捐納盛行的晚清社會,清廷也在通過種種制度設計儘可能保證正印官的素質,這就是計量能夠帶來的新啟示。
第二,官僚政治的空間分析。官僚政治史研究中,空間問題除了歷史地理學界有所關注之外,絕大多數學者並不是特別重視。特別是在分析地方官員時,往往偏重於官僚不同層級的結構分析,而不太注重地域之間的差異。在清代官僚全樣本數據的支撐下,對官僚政治的大規模空間分析,研究官僚政治的地域差異將成為可能。譬如可以利用GIS等新的技術手段進行清代官員升遷調動的空間規律的宏觀分析,對於大一統國家下如何理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如何合理選派官員以達到與任職區域的匹配、如何平衡邊疆與內地官員的升遷調動、如何對官員進行政績考核、如何協調本地升遷與異地調任的關係等問題展開探索。筆者先前曾對清代的政區分等及其對官員選任所帶來的影響,利用GIS空間分析手段,較以往清代政區等第的研究就有了較大不同,初步感受到了空間分析之於官僚政治研究的新的可能性。
第三,官僚系統流動性研究。其中至少可以包括兩個層次:一是官僚系統的來源。以往學者將其放在社會流動性研究框架內,研究官員與科舉的關係、官員出身與家族背景等,也不同程度使用了統計手段。不過這些計量數據總體來說比較有限。在清代官僚全樣本數據的基礎上,研究者更有利於將其與履歷檔、硃卷集成、鄉試錄等結合起來,從全樣本的角度對既往研究進行驗證和更新,對清代兩百餘年的社會流動性問題作出更加清晰、準確的界定,且可以將區域差異性分析納入其中。二是進入官僚系統以後的流動性。官僚系統的升遷調動一直是官僚政治史研究相對比較薄弱的部分,以往的研究只能針對具體人物展開個案分析,對於群體的研究一直無法開展。有了清代官僚全樣本數據的支撐,通過數據之間的連接,很容易梳理出大規模官員升遷調動的軌跡,必將為我們更深刻地透析清代官場選任的奧秘提供幫助,且幾乎是傳統研究方法無法處理的問題。考慮到社會學等領域對官員空間流動的研究也只是剛剛開始,那麼清代官僚流動性研究的學術價值與跨學科影響將更為顯著。
第四,政治網絡分析。在對官僚系統進行分析時,顯性關係是易於觀察的,如同年、同鄉等;而隱性關係則不易把握,如姻親、私人關係網絡等,特別是這些隱性關係在政治網絡當中的作用,一般比較隱秘,即使是當事人也未必形之於筆墨。如果研究者試圖從整體上去把握一定規模的官員群體時,困難就更加顯著了。大數據與社會網絡分析的手段有助於追蹤這些隱秘關係,學界目前利用中國曆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所做的政治網絡分析的成果已有不少。考慮到清代資料的豐富程度和官員數據的全樣本,對於清代政治網絡的分析將更具有實現的基礎。當然,解決這一問題,單靠官僚系統的全樣本數據還不夠,必須建設更多的數據系統並進行關聯,如官員之間的信札、名人序跋、家譜當中的家族網絡、同年錄等數據均納入進來,這將是一個長期但又深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方向。
作為一種新的探索,數字人文與傳統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的結合才剛剛開始,雖然具有美好的前景,但也同樣深具挑戰。
第一,清代官僚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目前《縉紳錄》量化數據庫基本建成,地方誌中的官僚數據庫建設業已開始,預計不久也可以完成。這兩個數據庫相互配合,可以初步建立起從清初到清末絕大部分官員的基本信息,包括任職時間、籍貫、出身等。但從研究需求來說,數據變量越多越好,可關聯的數據系統越多越好,可以說永無止境,需要學界花大力氣在數據的基礎設施建設上著力,特別是與官僚政治史研究直接相關的數據。如學界多關注到了履歷檔數據,但在清宮檔案中存在大量選官任官的奏疏,其中對於官員的履歷情況做了非常詳盡的記錄,由於這些檔案比較分散,信息點多且雜散,所以一向沒有得到學界過多的關注,其實其價值絲毫不亞於履歷檔。此外,類似硃卷、家譜中的信息,雖已見到學界有相關的數據庫建設計劃,但遲至今日仍然沒有見到真正公開、可用的數據信息。只有當清代官僚數據基礎設施完善以後,數字人文在清代官僚政治史研究中才能有更大的空間,才有可能帶來官僚政治史研究全新局面的出現。對於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要儘可能地邀請專業學者就其所長進行專業數據庫建設,另一方面也要積極運用知識圖譜等人工智能手段加以輔助。如對清實錄和地方誌的實體、關係、事件抽取,藉助人工智能技術進行官員信息的深度挖掘,在技術,上比較成熟並已在中國人民大學“基於地方誌的清代職官信息集成數據庫”項目建設中嘗試使用。
第二,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交叉研究。社會科學在當代官僚政治、社會分層等領域業已具有一系列成熟的理論、概念和方法,譬如關於當代官員的選拔、升遷、任用、績效的研究,在政治學、社會學、公共管理等學科中已有不少。社會科學非常嫻熟於定量方法的使用,且在定性與定量方法的結合上富有經驗。隨著清代官僚政治史基礎數據的建立和數字人文方法的成熟,可以說這一領域的研究不僅可與社會科學在理論與方法方面實現對接,而且還具有史學的獨特優勢,提供歷史縱深。兩者之間的融合不僅有益於歷史學科的方法更新,同樣可以與社會科學進行跨學科對話,進而為從長時段解釋中國的官僚政治運行提供幫助。
第三,傳統人文研究與數字人文方法的有機融合。其一,“數字人文”不是如很多學者批評的檢索史學,不是對史料解讀、考證傳統的拋棄,這是一種誤讀,傳統史學所強調的嚴謹考證,同樣是“數字人文”所需要的。其二,“數字人文”也不是一些學者批評的簡單呈現計算結果或驗證已有研究結論,而是通過計量發現新問題,促進對史料和史學問題的重新理解。可以說數據庫不僅是一種工具,也是一種新的思維,包括計量統計、空間分析等,都是傳統史學研究中較為薄弱的部分。它的引入,不僅不會損害傳統史學研究方法的價值,而是會為傳統史學研究增加一個強有力的工具,不能也不會替代傳統人文研究,我們更應該把數字人文看作是史學研究中如虎添翼之“翼”而不是同室操戈之“戈”。
第四,數字人文是否會重蹈“宏大敘事”的陷阱?數字人文不是傳統官僚政治史的簡單迴歸,而是為官僚政治史的再出發提供一種新思路。即使是用量化方法實現對政治結構的分析,這一結構不是統一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將變動與混亂引入,對政治現象的分析更多通過經驗考察來揭示而非通過空洞的數字和理論推演,更不會將某些政治史的普遍圖式作為歷史解釋的出發點,誠如米爾斯所說,“沒有任何“宏大理論’,沒有任何普遍圖式可供我們作為出發點,以理解社會結構的一體性”。新的官僚政治史研究所追求的是將個案的細緻分析與宏觀的計量結果同等看待,且尋求二者解釋的統一性,既會重視計量所帶來的便利,同樣會注重規避計量的陷阱,特別是從社會學等領域對計量的反思中吸取教訓,在定性研究與定量分析中尋求歷史解釋的平衡性。
數字人文對於清代官僚政治史的研究意義不止於官僚制度,也不止於政治史,而是要從新的視角,從傳統官僚政治中認識中國國家治理與中華文明的價值。當下人類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何解釋中國文明的普遍性與獨特性正日益成為學術界關注的重大問題,並對各學科既有研究範式提出了挑戰。數字人文時代提供了開拓“新政治史”的可能,特別是在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進行歷史文獻挖掘與研究及建立一套融合官僚政治“混沌”與“秩序"的複雜系統方面,值得進一步探索。
作者胡恆,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朱滸,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