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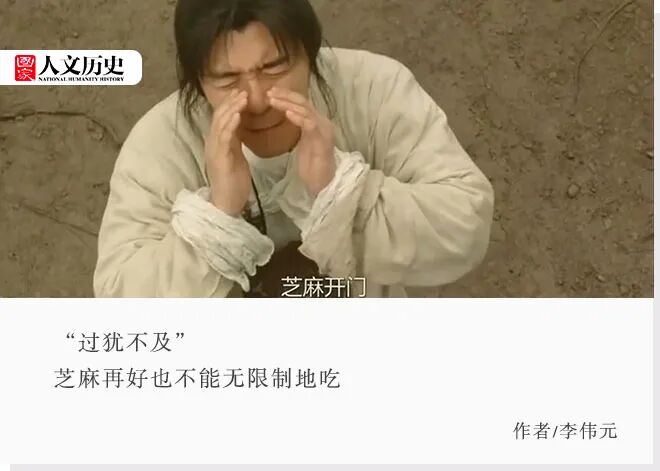
最近, 有關黑芝麻生髮的廣告又撩撥了一些人的心絃。實際上,老一輩早已口口相傳著同樣的信息:“多吃點黑芝麻,生髮!”於是乎,什麼黑芝麻丸、黑芝麻糊,盡情地吃吧。

可能在很多人心中,芝麻的神奇之處不止於此,更兼具一種神秘的“開門”功能。那麼,芝麻真的會長頭髮嗎?為什麼能叫來開門的也得是它呢?
野生芝麻屬植物的祖先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至今人工栽培芝麻仍然有著發達的根系,具有較強的耐乾旱、高溫特性。大約在5500年前,野生芝麻在印度次大陸被馴化,成為現在各國栽培的食用芝麻的源頭。公元前2000年,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之間已有芝麻貿易記載,古巴比倫人認為芝麻酒“給了眾神創造世界的力量”,也用它作為給神明的祭品。在古埃及紙莎草典籍裡也有種植芝麻的相關記載,認為芝麻可以緩解頭痛,芝麻油既能用來烹飪,也能用作化妝品,甚至為木乃伊防腐,在公元前1350年的古埃及圖坦卡蒙法老金字塔裡曾出土了一籃芝麻。
在上古時期不同的文化中,芝麻都被賦予神秘的寓意。最為人熟知的“芝麻開門”,來自阿拉伯古代民間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的故事,它是強盜掌控的寶藏大門的口令,換成“小麥”“豌豆”都無效,這可能來自於芝麻成熟時果莢裂開、種子迸出的場景。雖然一些其他植物散播種子也會有類似效果,但“鳳仙花開門”“三色堇開門”的效果聽起來都不如“芝麻開門”,畢竟芝麻對人們的作用更大。
阿里巴巴“芝麻開門”故事插圖。作者/Edmund Dulac
在印度教傳說中,芝麻種子是不朽的象徵,認為它是主神毗溼奴滴落的汗珠變成的,被視為獻給天神的“最純粹的祭品”。在印度教的火葬儀式上必須準備芝麻,由死者的長子或是祭司繞柴堆一週,將芝麻粒放入死者的嘴裡,祈求來世順遂。印度教傳統節日“瑪克桑格拉提節”慶典期間,教徒用芝麻油燃燈,祈求驅邪納吉,並用芝麻和堅果加糖做成球狀甜點,希望吃了它,開口都是甜言蜜語,處處能遇到好運氣。
我國古人想象的仙家食物中,用芝麻做的“胡麻飯”最常見。芝麻來自遙遠的西域,容易和神仙聯繫起來。而且芝麻的脂肪、蛋白質含量很高,有很好的飽腹效果,也能給人以服食神仙靈丹、不必再食人間煙火的感覺。古詩裡常以“松下飯胡麻”“胡麻作飯瓊作漿”來描述山中隱士的生活,無形中給枕流漱石的隱逸增添了一些煙火氣。
《天台志》記載,東漢永平年間,剡縣人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時採了桃子吃,感覺身體輕健;又看到溪水裡流下一杯胡麻飯,二人溯源而上,被仙女邀請相留。半年後劉、阮二人還鄉,不料人間子孫已歷經七世。《太平廣記》裡也有采藥民柳二公迷路,飢腸轆轆時遇見仙人,吃了胡麻飯、柏子湯的故事。
《神仙傳》記述一位“魯女生”(其實是男的),堅持食用芝麻八十多年,不吃其他穀物,面色紅潤得像桃花一樣,一天能走三百多里地。東晉葛洪在《抱朴子》中寫,堅持每天吃芝麻丸可以達到“一年身面光澤不飢;二年白髮返黑;三年齒落更生;四年水火不能害;五年行及奔馬;久服長生”的效果。蘇軾在《服胡麻賦》(題目對hf不分的人不太友好)裡高度讚頌食用芝麻的好處:“乃瀹乃蒸,甘且腴兮,補填骨髓,流髮膚兮”。
古人還用芝麻作為主要原材料之一,做出了高熱量的“能量棒”。比如用芝麻粉、糯米粉、棗泥和柿餅泥做成丸子,名曰“仙果不飢”,在外出吃飯不便時,吃上幾丸,足可以橫掃飢餓。
在我國古代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來自西域的芝麻都被稱為“胡麻”。《齊民要術》等記載,芝麻是西漢時張騫出使西域,從西亞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十六國時期,後趙皇帝石勒避諱“胡”字,將胡麻改名為“芝麻”。唐宋時期一般將芝麻寫為“脂麻”,或是繼續叫成“胡麻”,元明時期,“芝麻”“胡麻”仍然並稱,清代才基本固定為“芝麻”。不過也有一種說法是“胡”有“大”的引申義,因為芝麻比中國原產的麻類植物普遍要高大,故得此名。古人認為芝麻會使其他草木根株腐敗,所以在開荒地後要先種芝麻一年,再種其它作物。

芝麻植株下層的花先開,所以民諺說“芝麻花開節節高”。來源/pixabay免費正版素材庫
芝麻種子雖小,植株卻能長到近1米左右,莖有四稜。東漢、三國時稱芝麻為“巨勝”“藤宏”“方莖”等,都與它的植株外形特點有一定關係。而“狗蝨”的別名,形象地體現出芝麻種子的特徵。另外,古代芝麻還有別名“青蘘”,蘘字通釀,意思是它的葉片可以加工成醃菜食用。當然,它和沙拉里的“芝麻菜”並不是同一種植物。在芝麻種植大省河南,人們習慣在芝麻開花時節,將生長在植株中下部的新鮮芝麻葉擗下來,這不僅有助於養分集中到種子上,還能多一道有特殊香味的美食。芝麻葉用開水焯過後,揉搓掉苦汁,曬成乾菜,吃的時候再泡發,最適合下麵條。
北宋人莊綽給芝麻總結出了和別的農作物相比顯得“彆扭”的特點,稱為“胡麻八拗”,包括:陰天多雨產量低,乾旱天氣反而產量高;開的花向下耷拉,結的果實卻向上舉著;芝麻榨出的油叫“生油”,其實是把籽粒炒熟壓榨後得到的;如果把芝麻油塗在車軸上,能讓車輪運轉順暢,但塗在針頭上卻會讓縫補變得更艱澀。
芝麻雖然“拗”,但並不影響它的受歡迎程度。芝麻傳入中國後,最大貢獻之一就是改變了動物油為主要食用油的局面。芝麻種子平均含油率達40-60%,是同類作物中最高的,《物理小識》注中提到,二石油菜籽能榨油80斤,二石黃豆最多能榨油22斤,二石芝麻卻能榨油120斤。英語裡的“芝麻”一詞sesame來自於拉丁語sesamum,它可以上溯到古代閃米特語中的“油”。印度諺語裡形容人吝嗇到一毛不拔的程度,就說他像是被榨乾的芝麻,已經擠不出油來了。
古時芝麻油經常被叫做胡麻油,但現在通常說的“胡麻油”指的已經不是芝麻油,而是油用亞麻籽榨出的油,主要產自我國新疆、內蒙古、甘肅、山西等地。張賢亮小說《綠化樹》裡引用了西北民歌“芝麻胡麻出個好油,嫁不下好漢子我要維朋友”,體現出西北地區將兩種作物分得很清楚。
在油用油菜廣泛種植之前,芝麻油在我國古代使用的植物油中是當之無愧的“C位”,既可以用來食用,也能做燃料、潤滑等用途,三國時期滿寵用麻油澆灌火炬,以火攻擊退了孫權軍隊。唐代詩人劉禹錫還記錄了一個偏方,如果蚰蜒爬進耳朵,用麻油煎餅當枕頭躺下來,過一會蚰蜒自己就爬出來了。
早期榨芝麻油,主要是將生芝麻直接放入粗麻布袋裡搗壓,出油率很低;後來採用先將芝麻炒熟再磨碎榨油的方法,出油率大大提升。宋代還出現了一種更加精細的“水代法”榨芝麻油方式,將芝麻炒熟研碎後加水煮,因為油和水不相溶,油脂自然浮在水上。這樣得到的芝麻油格外濃香,將它塗在手心裡,能夠從手背聞到香氣。依靠越來越高效的制油辦法,芝麻油的產量穩步提升,用油煎、炒、炸的菜式隨之增加,大大豐富了古人的餐桌。《夢溪筆談》記錄了一個笑話:北宋時期北方人做任何菜都要用麻油煎,有個廚師沒見過蛤蜊,用麻油煎得焦黑,還納悶這玩意怎麼還不爛?

芝麻油。攝影/mnimage,來源/Adobe Stock圖蟲創意
在今天各地的日常菜譜裡,芝麻油一般用於調味增香,直接炒菜的時候不算多。但在中國臺灣仍有用芝麻油高溫烹飪的習慣,黑芝麻油、米酒、老薑三者的搭配被視為傳統“藥膳食補”的重要組成部分。用麻油將薑片、雞塊炒過,再用米酒代水煮成的“麻油雞”,營養豐富,是婦女產後的滋補佳品。
和虛無縹緲的長生求仙之道相比,富含油脂的芝麻更適合為人們的日常飲食增添驚喜。高脂肪、高糖分的組合,能夠極大地滿足人們的口腹之慾,因此各國都將芝麻作為甜點的重要原材料。
早在唐代,已經出現了“胡麻糖”,也就是現在我們說的芝麻糖,這種用黏稠的糖漿將芝麻結為一體的吃法,上千年來基本沒有改變。一口咬下,香、甜、脆在口腔中爆開,回味無窮。蘇軾還用蜂蜜芝麻丸治好了痔瘡,將去皮黑芝麻九蒸九曬,和茯苓、蜜做成藥丸,堅持吃一段時間,減輕了症狀。明人有詩描寫:“胡麻靈藥本仙葩,巧累浮屠鬥佛家。莫道此中無舍利,玲瓏顆顆現光華”,可能是一種做成寶塔形、用來供佛的芝麻糖。更精細的蘇州傳統細點“黑麻酥糖”,是將炒熟的芝麻研磨成粉後加糖製作的,質地鬆軟,入口即化。
宋人習慣將芝麻加入茶盞,至今湖南鄉間仍然有在茶里加入姜、炒豆子和芝麻的喝法。順滑香甜的芝麻糊,也是嶺南的經典甜品。芝麻放在點心裡,無論是做餡料還是貼在表面,都有極好的增香效果。東漢“胡餅”的一大特點是表面貼有“胡麻”(芝麻),自漢靈帝到平民百姓,人人愛吃。唐代時胡餅的流行程度不亞於今天的網紅店,都城之外的餅鋪也都在模仿長安的做法,白居易慷慨地將胡餅分贈給友人並題詩:“胡麻餅樣學京師,面脆油香新出爐”。北宋開封的胡餅有“門油、菊花、寬焦、側厚、油碢、髓餅、新樣滿麻”等不同種類,各個餅店五更起和麵做餅,有的大店甚至有50多個烤爐。宋代以後胡餅的叫法雖然少見,但吃法卻流傳至今。清代有竹枝詞歌詠江南點心:“搓粉和糖油炮烙,外旁還摻黑芝麻。”
黑芝麻餡湯圓現在最常見,不僅因為好吃,也因為餡料製作較為方便。來源/pixabay免費正版素材庫
芝麻炒熟研磨製成的芝麻醬,是北方人鍾愛的調料,可能尤以北京為最。作家老舍曾經寫過特殊的政協提案——為北京市民申請充足的芝麻醬供應!紅學家鄧雲鄉也認為:“我平生塞北江南,所到之處,再沒有看到比北京人更愛吃芝麻醬的了。”清末義和團民歌裡唱:“芝麻醬,蘸白糖,鬼子最怕董福祥”,這一吃法在電視劇《我愛我家》裡也有體現,和平失憶之後,最想吃的就是:饅頭片上厚厚地塗一層芝麻醬,再厚厚地撒一層白糖。由於純芝麻醬成本高,幾十年前北京的糧油店售賣的以“二八醬”為主,據說芝麻的比例只有20%,大部分是花生醬。
儘管如此,北京日常飲食確實很難離開芝麻醬。芝麻醬燒餅、芝麻醬糖餅自不必多言,就拿火鍋來說,傳統的老北京涮肉鍋底基本為清水,薄薄的羊肉片、鮮嫩的白菜、柔韌的粉絲涮好之後,芝麻醬蘸料增添了醇香的滋味,還能減緩滾沸食材的燙意。但這一蘸料似乎並不太受南方人喜愛,川渝火鍋仍以香油蘸碟為正宗,如果請服務員來點兒麻醬,很可能是送上一瓶沒開封的芝麻醬,讓食客自行調配。其實,瓶裝麻醬直接做調料過於粘稠,需要將適當的麻醬放入碗中,加入涼開水攪拌,這一過程叫做“澥”,澥到筷子無法挑起的液態後,加點鹽調味,才適合涮火鍋、蘸爆肚、拌麵條。連麻辣燙傳播到北方後,調料裡也加上了芝麻醬,一定程度上起到緩解辣味的作用。
在夏天,一盤澆了芝麻醬、花椒油和熗芥末,放了黃瓜絲和豆芽的過水麵是北京人的最愛,脂肪和碳水的搭配帶給人很強的飽腹感和滿足感,吃起來又足夠清爽。武漢人過早(吃早飯)首選熱乾麵,儘管和它的基本原料相似,但芝麻醬的質感更加濃稠,作料也更豐富。在一次性紙碗裡裝好,撒點酸豇豆或是蘿蔔乾,邊走邊拌(武漢話讀ben)邊吃。

北京傳統的“麵茶”用糜子面熬成稠稠的糊狀,除了糧食的自然香味,沒有其他的味道,提味全靠芝麻醬,“用兩根竹筷子,把紫銅鍋裡特製稀釋的芝麻醬蘸起來,以特殊的快手法,把芝麻醬撒滿在麵茶上面”(唐魯孫),芝麻醬還能起到保溫效果,喝到最後一口仍然是熱乎的。
在北京的近鄰天津,芝麻醬又有新的吃法,雞湯打滷豆腐腦,端上桌之前少不了一勺芝麻醬;撒滿香菜和滷汁的鍋巴菜,如果沒有芝麻醬就像是沒了靈魂;過年的素餃子拌餡時也要放芝麻醬、香菜、紅腐乳調味,煮好後有著特殊的濃郁香味。
中東、北非、地中海沿岸和外高加索等地也吃芝麻醬,但裡面的調味品是檸檬汁、大蒜,用來抹面包、拌沙拉、拌鷹嘴豆泥、配烤魚和烤茄子,都是上選。
古人認為“胡麻都以烏者良,白者劣爾”,現在通常黑芝麻醬、黑芝麻油賣得也更貴。不過,黑芝麻一定比白芝麻好嗎?
在我國,黑芝麻和白芝麻的主產地不同,白芝麻主要產自中部地區,在芝麻市場上數量最多;黑芝麻主要產自華南,因為總的產量較低,也影響了價格。儘管古人試圖用“寒熱性”來區分黑白芝麻,並且在人們日常認知中,似乎黑芝麻顯得更有營養,對減少白頭髮更有好處,但其實二者的營養成分沒什麼顯著區別,顏色的差異主要來自於黑芝麻種皮中的兒茶酚類和花色苷,它們是芝麻表皮黑色素的來源。另外,吃下去的兒茶酚並不能精準作用到提高毛髮的黑色素水平上。
而且,芝麻再好吃也不能無限制地吃,如果過量吃芝麻,不僅不能生髮,還會導致脫髮。古人認為吃芝麻能“生禿髮”,是建立在古代多數人營養不良的基礎上的,芝麻中富含多種微量元素,蛋白質、亞油酸等物質含量也很高,在其他營養攝入不足的情況下,吃芝麻當然有助於促進頭髮生長。但對營養普遍過剩的現代人來說,一勺芝麻相當於半碗米飯的熱量,如果吃過多的芝麻,相當於攝入過量的脂肪,增加頭皮油脂分泌,造成毛囊堵塞,反而加重了脫髮的症狀。據央視報道,市面上售賣的“黑芝麻丸”生產許可證是普通食品生產許可證,並不能替代保健品。有的顧客一年買黑芝麻丸的錢,可以購買兩三百斤黑芝麻。
被中國人食用近兩千年的芝麻,儘管承載著虛無縹緲的神仙傳說,但令人銘記的始終是它特有的“煙火氣”,曾經讓尋常食物的滋味變得更為豐富,給過往清苦的歲月增添了芬芳的回味。但在餐桌高度豐富的今天,芝麻雖好,還是不能貪吃。
韓茂莉.歷史時期油料作物的傳播與嬗替[J].中國農史,2016,(第2期).
徐龍,哈馬爾罕.幸運的食物 ——芝麻[J].餐飲世界,2022,(第11期).
端木東舸.芝麻醬的江湖地位[J].北京紀事,2022,(第4期).
脫髮後狂吃黑芝麻 不料脫得更嚴重了.承德晚報.2022.06.13
央視揭秘脫髮焦慮下的芝麻丸一族.武漢晚報.2022.03.23
*本文系“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讀者轉發朋友圈。